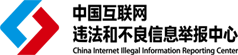君子不抓机会主义
□刘诚龙
朱熹之才,宋宁宗先前是没“朕亲见之”,却是天下都见之,天下见之而皇帝不见之,也是多的,朱熹后来让宁宗“朕亲见之”,缘起宁宗一班旧臣如陈傅良、彭龟年、黄裳、罗点,尤其是赵汝愚等亲见之。赵汝愚当了宰相,他要组织一套好班子,便向宁宗推荐了朱熹。宁宗是蛮高兴的,宁宗没见过朱熹人跑,他是见过朱熹才跑的。朱熹才气纵横,名满天下,宁宗当然听说过。
宁宗是初登位,新官上任想烧烧火。宁宗于是对他东府一班旧臣下了招贤令:“朕初承大统,未暇他图,首辟经帏,详延学士。”宁宗想办个经筵学院,想请帝王师,来教教他治国安邦。自然,领导要请的帝王师,当是无双国士来当其国师,朱熹是不二人选。
多好的机会啊,不是我要去,是领导喊我去,这机会千载难逢,这机会万人不有。多少人削尖脑壳想去找领导,这里领导亲自喊他,他屁股自然颠颠的了。宁宗打发人来喊朱熹,曰:“主上虚心好学,增至讲员,广立课程,深有愿治之意思。”朱熹喜得打跌,“果如此,则国家万万无疆之福,义不可不一往。”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宁宗貌似还是蛮诚恳的,朱熹兴冲冲去了宁宗家,宁宗开诚布公,喜滋滋对朱熹说:“若程颐之在元祐,若尹焞之于绍兴。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朱老师啊,我是真心实意要请您指教我的,您尽管将您“正心诚意之说”无所保留地教我。领导真这么说,谁都感激涕零。朱熹好生认真的,认真备课,认真写教案,一口气备了十堂帝王课。第一课是“论经权常变”,第二课是“帝王之学”;第三第四课,都是正心诚意的学问。
宁宗之前学习是蛮认真的,学习精神蛮强,对朱熹说,我们师生不放假,分单双日吧,单日是上午学,下午也学,双日可上课也可不上课;朔日(初一)与望日(即十五)还是放个假。朱熹教学热情特别高涨,他说,还是课程安排满一些吧,除朔望与双休日(时谓旬休与过宫日),其他不分单日与双日,都开讲。朱熹恨不得将其学术一股脑儿全灌输给学生。朱熹当老师,可以评优秀教师啊。
所谓厕所板三天新鲜,宁宗读书也是三天新奇。朱熹真把自己当帝王师了,没想到宁宗已然有些烦躁:朱熹“急于进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切,颇见严惮。”朱熹在讲台上常常板起脸当严师,朱熹不但是上课时候常给宁宗念紧箍咒,便是宁宗出台什么政策,他都要利用课堂教学对此教导一番。比如,宁宗打算起用韩佗胄,朱熹便训导宁宗:要亲贤臣,远小人。比如宁宗想建个楼堂馆所,朱熹又板起脸: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宁宗最初学习新鲜感过了,便对朱熹特别厌恶起来。朱熹看不出宁宗态度有变,韩佗胄却是最善察言观色,看到宁宗眉宇间对朱老师嫌弃,便趁宁宗皱眉,进起了谗言:“朱熹迂阔不可用。”是啊是啊,朱熹真把自己当玩意了。算了,不学习了。宁宗对朱老师说,现在冬天了,天冷,您回家吧,别冻了您老人家了,从明天起,您别来上课了(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冬天不用春耕,正好可学习嘛。学你个鬼脑壳:“今乃事事欲与闻。”故,朕要“除朱熹经筵。”
朱熹意洋洋地来当帝王师,只是当了四十多天,便被宁宗赶了回去。
多好机会啊,领导请他去领导身边,这个机会没几个人有,干嘛不紧抓在手呢。一朝选在君王侧,足可以日专日来夜专夜。领导喜欢什么,你就奉承什么嘛,他却偏偏与领导过不去;领导喜欢青楼,你楼下站岗;领导喜欢桥牌,你桌边数笋;领导喜欢踢毬,你球场捡毬;领导喜欢阿谀,你肚子里那么多词语,颂词都不会用吗?如此,改天外放当藩镇大员,京升为六部九卿,或者更可以由帝王师转宰相府,也是概率大大的。
许多人都是这样干的。比如高俅,本来是街头混混,机缘偶得,会踢一脚足球,跟先前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联系上了,端王踢球,他就陪他踢球,端王大吃大喝,他就陪他喝酒吃王八,当端王贴心人,当端王心腹蛔虫。看看,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家伙,后来当了好大好大的官。
朱熹历史上多多少少有些非议,但他形象并不过分难堪,后人还将他列入圣人之列。其故也,朱熹对机会,有其正念也。其正念者,抓机会,不抓机会主义。君子者,抓机会或不抓机会,但一定不抓机会主义;小人者,抓机会,特别抓机会主义。何谓机会主义者,便是领导喜欢什么,他奉承什么;领导不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以娱领导为能,以媚领导为是,什么正心诚意,机会主义者是没有的。
有谓,个人操守在当时官场屁都不算。官场升沉,或者官人形象,没谁看个人道德,只看政治立场与情感倾向。司马光、王安石与蔡京、秦桧一样,都曾经被打为奸臣。道德有甚用呢?此言也是差矣。司马光确是有人要对他起棺戮尸,要把他从黄土里挖出来,挫骨扬灰;王安石得罪了千万人,当时人人臭他,但后世评价光老与荆公,形象还是很正面,其故也,政治下了庙堂,道德便开始上讲坛了。朱熹不搞机会主义,他坚持自己学术品格,不看脸色行事,确乎给他造成了麻烦,前途因此被毁了,但朱熹的形象没被毁,至少朱熹其做帝王师中表现的个人气节,后世没谁臭他。
现实表现也许会害了君子们的前途,个人操守却可以救起君子们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