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儒曾廉与《牂柯客谈》
□姜秀波
民国总理熊希龄的老师、《大清会典》的编纂者之一、晚清名儒曾廉,清末之际曾经隐居在“黔之东鄙”(今黎平、锦屏一带)长达数年,期间完成了贵州地方史考证文集《牂柯客谈》的撰写,为今天研究贵州地方史及少数民族古代史留存下重要参考文献。
晚清名儒的“两面性”
曾廉(1856-1928),字伯隅,号非斋、㼖庵,湖南宝庆邵阳县(今湖南邵东市汪塘乡牛山村)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翌年会试后,任国子监助教,参与编修《大清会典》,为大学士徐桐赏识。“庚子之变”期间,“以知府参督师李公幕”(见《?庵集序》),后获授陕西补用知府,寻“以劳迁道员”留省,后被革职。
曾廉是清末顽固保守派,极力反对变法革新。
中举前,居乡期间,时雀塘铺(今新邵县境内)人樊锥在邵阳组织“南学会”反旧教,倡新学,曾廉于邵阳学宫会集群儒斥樊锥“倡邪说,背圣教”,将其驱逐出邵阳。中举后,会试落第、宦京期间,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曾廉则上书清廷,指责康有为、梁启超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
宣统二年(1910),曾廉隐归,重返故乡,主持杨塘书院达十六年之久。其时已废科举,兴学堂,但曾廉仍力倡旧学,尚孔孟之道,以“仁学”自勉。
是故,民国湖南文史专家李柏荣在《记曾廉事》中曾论曰,“吾邵治学能取进士者,以曾廉为最迂”。对曾廉“竟不知时务”,后人莫不惋惜。
但同时,面对外国列强入侵,曾廉也曾是坚定的主战派。
早在“庚子之变”,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师败”(清军落败),曾廉“沉河不死”,即“仓皇”西逃。待1901年慈禧太后“‘回銮之议’起”,曾廉“以为此兴亡所关,不可不力争,遂上疏极谏”,然而,等来的却是“不听”(见《?庵集序》)。
曾廉曾上书言战,为“乘舆既东用争者”忌恨,待《辛丑条约》签订后,即“恶其始终立异,因诬以罪”(见《?庵集序》),最终“着革职,永不叙用”(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续录》)。
对“乘舆既东用争者”的“诬以罪”,曾廉积愤难平,却无力抗争,选择归隐他乡。
尽管仕途不尽如意,宦海覆舟,但曾廉却阴差阳错地“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得以著述等身,有《?庵集》《?庵续集》《元书》《元史考订》《禹贡九州今地考》《牂牁客谈》等文集传世,又培养出了民国总理熊希龄等一批国之栋梁。
其一生忧国忧时,颇具家国情怀、历史情怀和文化情怀。
梅屏山麓的“掘阅堂主”
清末之际,风云变幻。曾廉因上言主战、力主抵御外辱,被清廷革职查办,后携子逃遁至贵州黎平、锦屏一带,筑室于黎平、锦屏之南的梅屏山麓,隐居授学著述数年,直到宣统二年(1910)方才返乡。
对隐居黔东事略,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廉在其所撰《牂柯客谈自序》中仅有寥寥数语:“余寓居于黎平、锦屏之南梅屏山下……”
而曾氏人撰于宣统二年(1910)冬的《?庵集序》则述之甚详:
……与知交别于沙洋,独携其子,□踰洞庭而南徏,步数千里,止于黔之东鄙,变姓名,授徒自给,而名其园曰“掘阅堂”,日有枢,而各为之文以寄意,泊然若不知身世之何属者。然于天下事,或有所闻,未尝不苍茫感喟,歌哭无端,以抒其忧愤,而亦往往汎滥于庄周、列御寇之闲,为恢诡离奇不可端倪之说,盖其辞溯而其旨愈深矣!
籍此可知,曾廉改换姓名后,携子长期寓居于梅屏山麓,以“授徒”为生计,然终“位卑未敢忘忧国”。期间,“日有枢,而各为之文以寄意”,著述颇丰。
宦海浮沉,矢志不渝。可以说,经历国殇期间“沉河不死”,以及被“诬以罪”之后,曾廉在忧愤中以史学建树成就于“黔之东鄙”的梅屏山。
湘黔交界地带的梅屏山,今已无可考。但据曾廉所述,可以确定该山在“黎平、锦屏之南”,亦即今之黔东南。而其园“掘阅堂”,以及其所授生徒,今亦渺无可考。
作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掘阅堂堂主,曾廉的诗词,有相当造诣,亦可见其斯时心境和情怀。兹录其《摸鱼儿·咏事》:
艳阳天,小桃开了,碧栏干外有凛。芳汀回看,鸳鸯伴,妒杀鹤寒鸿?。
人早审。萼绿去,人閒那得神仙品。香凝燕寝。是再世情缘,三生福分,莫认旅窗枕。
闺房事,谁道鸣鸠醉椹。频年犹未能稔。妆台宝镜分明是,忽忽积尘如恁。君不尤。从古昔,机丝萋斐空成锦。谗人太甚。只瑟怨琴凄,同埋玉树,残魄恨犹饮。
这首词,通过春日景色、闺房情景等诸多意象,抒发了曾廉在宦途际遇、命运等方面的失意孤独和哀怨无奈,以及对谗言诋毁的愤恨和对未来的向往等复杂情感,足见隐居期间其心中难以抑制、无法言表的忧郁和愤懑。
恢诡离奇不可端倪之说
以《?庵集》《?庵续集》,称曾廉为词人、文学家,可也;以《元书》《元史考订》,称其为元史学者,可也;而以《禹贡九州今地考》《牂牁客谈》,称其为地方史学者,亦可。
曾廉居黔期间所著《牂柯客谈》,全书计二百三十多页,共分七卷。
其卷一为“表格”,卷二为“地图”,卷三为“总论”,卷四为“水道”,卷五、卷六为“地形”,卷七为“故事”,对贵州古地、古江、古族,又夜郎、牂柯、西南蕃、牂柯蛮,以及谢氏、赵氏、龙氏、宋氏等的来历和今地今族等,均有所考证。
《牂柯客谈》中,图、表、文等诸体例完备,有引有据,有考有述,兼收并蓄,断非虚妄的“率尔操觚”之作。
实际上,如此成体系地对牂柯历史全面、综合的考证,在晚清民国学术界并不多见。
《牂柯客谈》系清光绪年间刻本(《邵阳曾氏三种》刻本),现今存馆藏文本。
“余尝考历朝诸志,而后叹汉唐人之识之精确,而明人为最荒也。”在遍考历朝诸志关乎牂柯的前人考辨之后,曾廉认为,对牂柯历史的考据,汉代、唐代的学者见识精确,而明代学者的见识则最为荒疏。
在京师任国子监助教期间,曾廉曾参与编修《大清会典》,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历代各地志书。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余尝考历朝诸志”,这为他后来撰写《牂柯客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廉对“牂柯史”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换言之,其所著《牂柯客谈》,系站在文献学、考据学的基础之上,通过严谨论证而成,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民国二十七年(1938),拓泽忠修、周恭寿纂的《麻江县志》,就曾关注到《牂柯客谈》,内中有“近人曾廉作《牂柯客谈》,曾定都江为康谷水”之言。
也就是说,民国期间的贵州学者在编纂地方志时,曾兼考过《牂柯客谈》。
其辞溯而其旨愈深
曾廉虽因恪守旧学观念被时人诟病“迂腐”,其在宦途中坚持守旧的主张也被指“不知时务”,但这种时代认知的局限性,并未掩盖他在学术领域深耕细作所取得的斐然成就。
曾廉认为,其所寓居的“黎平、锦屏之南梅屏山”之下,“盖汉之镡城地,属诸武陵,未尝隶牂柯也”。籍此,曾廉论曰“然今称贵州全境皆曰牂柯,不复知其东境之为武陵也。”
其进一步论述,得出“而汉之牂柯,西境则至于今云南之东,与今之以贵州全境名牂柯者,皆不合”的结论。也就是说,曾廉认为汉之牂柯,其东境至今黔东止。而今黔东之一部分(黎平、锦屏一带),则应为武陵境。
换言之,曾廉认为梅屏山所在的黎平、锦屏一带,为古之武陵,今之牂柯。
一言以蔽之,即曾廉否定了“今称贵州全境皆曰牂柯”之说。当然,其所言“今”,指的是其著书时的清末年间。
是故,曾廉在自序中有言,“余书称《牂柯客谈》者,合古今而为名也。”
《?庵集序》的作者论曾廉居黔期间所著“恢诡离奇不可端倪之说”,实际上“其辞溯而其旨愈深”。斯言诚哉!
实际上,曾廉在经史考据、文献校勘等方面的力道,以及建立在遍读“历朝诸志”基础上的独到见解,都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成果,时至今日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漫长的岁月剥蚀中,曾廉当年所考见的部分古籍史料已经散佚无传,故《牂柯客谈》的部分“引”和“据”,在今天已属难得一见。或可以说,其无意中填补了文献史料中关于牂柯记载的一些缺漏和空白,对厘清黔境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多有补益。
目前,《牂柯客谈》尚未见点校本面世。曾进入贵州学界视野,后长期被“束之高阁”的《牂柯客谈》,将会给贵州地方史及少数民族古代史研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值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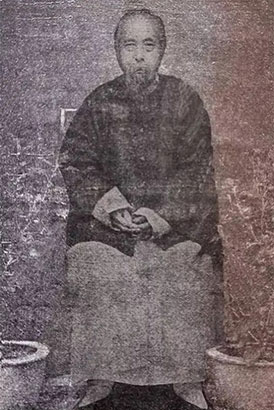
曾廉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