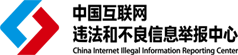编者按
传统中国画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方文明的艺术现象,是有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独特体系的。但由于一个世纪以来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风气,很少有人注意这个体系的存在。国画界中人往往一叶障目,把局部当整体,把分枝当干流,把现象当本质。从中国画系统的角度看,该系统可看成是由缘情言志的本质特征决定意象造象的原则机制,由此再决定或制约中国画的题材选择、结构安排,技法和材料运用,然后才是作品生成后的风格特征等四个有机构成部份。由此四个部份共同构成整个中国画的完整系统。但这个系统中,情志的内涵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题材、结构、技法、材料层次,风格层次也是不断变化的,而意象造象的原则机制则是相对恒定的。我们守其所当守,变其所当变,古老的中国画就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葆民族艺术无限的生命力。
中国古典绘画体系中意象造象的原则机制
——对中国古典绘画体系核心机制的研究
□林 木
经过一个世纪对民族文化视作冠仇的全民性荒唐之后,要 “重拾旧山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民族绘画传统的理解与继承上,就出现过许多糊涂的倡导。例如许多人正气凛然地把笔墨当成中国画的底线,有的又同样正气凛然地把宣纸水墨当成中国画的正宗,又有人把逸笔草草的写意而且是大写意当成中国画的正脉,亦有人把以书入画书法用笔当成传统绘画之正统……人们在倡导或主张这些观念时,往往都颐指气使,一副唯独自己得道真理在握的凛然神气,其他任何另有他途的画家不是旁门左途,就是邪门歪道!但如果真正认真地研究过中国美术史,认真研究过中国美术传统,当知道笔墨至上倾向出现于明末,写意作为倾向出现于元代,大写意出现于明代中期,今天这种发散性质好用于水墨写意的宣纸出现于明末清初,水墨倡导于唐兴起于南宋,以书入画的倡导出现于中唐……亦即所有这些节点出现之前,上述那些绘画现象作为潮流倾向都未曾出现,中国传统绘画一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多种倾向。而即使上述这些倾向出现,也不意味着其它趋向的消失。例如笔墨至上的倾向始于松江派“董其昌、陈继儒”们的倡导而盛于清初“四王”们的身体力行;而松江派之前绘画界是以意境的意造为主脉的。就是笔墨流行之后,石涛、八大,甚或“清六家”们自己也并未废意境的表达。况且在传统美术中,还有非文人画的民间绘画、佛教道教绘画存在,此类绘画数量及在民间的影响都远远地大于文人画!尽管他们并未纳入文人所书写之美术史,但作为美术史的客观历史存在,他们当然也应当是中国古典美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但经过西方式“一分为二”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熏染的今人,既弄不清古人究竟做了些什么倡导了些什么,也未能完整而客观地把握美术史,就经验式的把离我们最近,而标榜得又最厉害的明清以来的文人画及其特征当成了整个中国美术传统的正宗正脉!这种严重的学术偏见,根源于在一个世纪的民族虚无思潮之后,人们对民族传统严重地缺乏了解。而一叶障目,把局部当整体,把分枝当干流,把现象当本质。
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文化界有一股民族文化的复兴思潮,其中,美术界、美学界对中国美术传统就有相当深度的研究。其中一些对中国美术本质的研讨比今天就深多了。例如,林风眠早在20年代,就认识到,“东方艺术,是以描写想象为主,结果倾于写意一面”,“东方艺术,形式之构成,倾向于主观一方面”。他在1936年更在自觉探究“应该知道什么是所谓‘中国画’底根本的方法”,可见林风眠比今天的传统派更关注美术传统之“根本”与本质。在他看来,因东方艺术之主观与想象之根本,才有写意或抽象一类特征。林风眠是想探究中国艺术的本质的,这点,美学家当然更有优势。1943年,美学家宗白华在其《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提到清代画家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的一段话:“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 并指出“中国绘画的整个精粹在这几句话里”!既然“中国绘画的整个精粹”就在其中,那是其中的哪些关键词呢?显然是“因心造境”之 “虚境”, 是“蹈虚揖影”,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之灵境。可见,心灵是中国“造境”之根本,是中国艺术境界之根本。在另一处,中国美学界这位最为睿智而诗化的哲人又说,“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一境层”。这里“诗境”是中国绘画的“灵魂”。宗白华这位学贯中西的睿智的哲人已经把握住了中国绘画的“整个精粹”!他由这个核心灵魂出发,指出中国绘画所绘之景不是“实境”,而是“蹈虚揖影”之“虚境”,中国绘画的空间 当然也就“是一种永恒的灵的空间” ,“是以一管之笔,似太虚之体。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是绘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 “《易经》上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中国人看山水不是心往不返,目穷无极,而是‘返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
宗白华已经把中国画最根本的东西说得很清楚。其实,这种“心灵”传达的中国文艺特质,在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中就已说得很清楚。有三千年左右历史的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之说。此“志”据郑康成注《尧典》“诗言志”为“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照闻一多的意见, “诗言志”最初应该有记史的意思,但到距今三千年左右之《诗经》的时期,“诗言志”“应该统名之为陆机《文斌》所谓‘诗缘情而绮靡’之情,古人则名之为意”,以及“情思、感想、怀念、欲慕等等心理状态”。汉代《毛诗序》论及青铜时代之诗时则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朱自清先生把《尚书》的“诗言志”当成“中国诗论的开山”。可见中国文艺几乎从有理论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主观心灵情志对艺术的主宰作用。当然,“诗言志”已是对《尚书》出现之前的中国艺术本质的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从包括彩陶在内的原始艺术及《尚书》所处的青铜艺术时代,那神秘而崇高的巫术崇拜祖先崇拜的强烈的精神和情感内涵,也一直是主宰被后世称作艺术的原始彩陶和三代青铜器的制作的。
这种把主观的精神性因素放在艺术第一位的性质,当然就形成中国艺术在本质上与其它民族艺术的区别;而把精神性因素当成绘画的主宰,又必然形成相应的艺术创造的原则机制。那么,中国式的艺术思维及原则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前述宗白华所激赞的“因心造境”的方式。中国艺术美学重 “象”而不是“形”。《周易·系辞上》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尽意之象为之意象,未有意之形仅为形器。庄子说得更直接:“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照中国远古这些哲人看来,仅有外在形色的器物其品格是低下的,只有“形形之不形”(《庄子·知北游》)时,才可谓“形而上者”“尽意”之“象”。此“象”即老子 “无形”之 “大象”。所以,最近有学者认为,西方式的视觉意义上的“造型”,与中国绘画美学中“立象以尽意”的以意“造象”是有着本质上的重大区别的。然而中国之“象”,如《易》所称:“是故《易》者象也,象之者,像也”;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中国之象亦是取诸大千世界之物象,但由于为了 “尽意”而“立象”,此象就又非形而下之形,亦非纯视觉之视象或实象,所以宗白华引方士庶所说之“因心造境”,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都是此种 “意象”的生成方式。
既然要“因心”而“造境”,要“尽意”而“立象”,中国艺术之造象方式当然与西方摹仿自然的造型方式大相迳庭。西方可以去研究用投影用透视用解剖用光学、色彩学,用各种“科学”手段把自然摹仿得唯妙惟肖,但中国艺术家作画的目的根本就不在再现“形而下”之“器”,而专注在“形而上” 之“道”上。然载道之手段仍在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之“形”有关之“象”,那由“形”至“象”的升华途径何在?
象征是重要的手段之一。除少数实用功能性需要的写实外,中国绘画中很少有画什么就是什么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说的就不是鸟,这叫“比兴”,是以鸟说事;同样的“山水以形媚道”,(刘宋.宗炳)山水画是用来亲近道的载体,牡丹象征荣华富贵,鹤妻梅子,梅兰竹君“四君子”都是象征,宋徽宗那么写实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竟也是政治与道德的喻意。就连那些《采薇图》《高逸图》《兰亭雅集》一类人物画母题,也都是古典文人理想之象征……
既然是象征的手法,则表现对象就已经不再是试图客观再现的真实物象的代用品,而仅仅是某种情感、精神、观念等主观因素的符号。符号性成了中国绘画造象特征之一。不要说一些形象性的因素,如文人性质的山水、花鸟,在民间艺术那里,则差不多每个形象,每个物件都是符号的象征,如“年年(莲)有余(鱼)”,如“富贵(桂)平(瓶)安”,“五福(蝠)捧寿”、“马上封(蜂)侯(猴)”等等。其实,就是金碧、水墨,又何尝不是皇家富贵,道家哲理和文人雅逸的符号呢?
符号的象征性质和他的指事功能自然地使它产生了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特殊艺术形态。亦如远古源于自然的象形文字是符号一样,半坡陶盆上的三角纹是对鱼的抽象,彩陶中庙底沟的叶形、花纹形是对植物的抽象,而马家窑彩陶上那流转无定的漩涡纹、垂幛纹以及后世青铜器上的饕餮、窃曲纹又何尝不是东方先民们那高度发达的源自现实某些物象的抽象的创造呢?当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时候,当我们得益于以书入画的传统特征的时候,当我们在用水墨去表现本该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强调和信奉笔墨至高无上的审美功能、“本体”和“底线”的功能的时候,不正是有这种六千年抽象审美意识的民族底气在起作用么?
抽象是其对客观具象的简化、变形、夸张、提炼等方式而言,然此抽象与西方建立在数理或视知觉基础上的彼抽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抽象的结果,自然又会形成超现实的虚拟性特征。所谓“虚拟性”,即指中国人固然也在“反映”现实,但却没有真实地可触可摸可感地幻觉地再现现实的企图。中国绘画中的以线造象是虚拟,留白是虚拟,朦胧、恍惚、虚、空是虚拟,整个中国画之“蹈虚揖影”之“虚象”也都是虚拟。
象征、符号、抽象、虚拟诸性质又必然导致中国绘画出现较为恒定的有固定意味和固定形式的程式化倾向,中国艺术的程式化倾向是十分突出的。中国文学中的诗词格律,文体中的起承转合,戏剧中的唱腔、脸谱,体态身姿中的一招一式,无不具程式性特征。绘画中的各种程式,则只要翻翻《芥子园画谱》就可一目了然:各种皴法、叶法、树法、点法、三远法,笔墨中的各种线描之法,如“十八描”中的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线描、行云流水描、钉头鼠尾描、折芦描、柳叶描……程式呈现出一种意味,对程式的创造性运用当然是传达或获取特定文化意味的有效手段。
符号、抽象、虚拟、程式种种写实特征必然形成于一种画面结构上的平面结构关系,而使中国绘画这种按西方分类上本该属于空间艺术的艺术样式呈现宗白华所称之“灵的空间”的特征,使中国传统绘画摆脱了本来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的立体的透视的具深度视幻觉的画法,摆脱了这种泛人类视知觉常理的画法,而自由地平面地在画面中结构安排情感传达的意象符号。中国人心鹜八极,神驰四荒,难以一不动之视点限之,故有“三远”之法,曰高远、深远、平远,曰幽远、阔远、迷远,以致又有纳时空交错之多角度多画面随心所欲于一画者,非平面的摆布又何而能为?此为传统绘画平面性特征。
传统绘画的装饰性性质当然也和上述诸特征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抽象性和虚拟性的存在,中国绘画具有典型的超现实性特征,中国画家们在面对现实时完全没有拘泥于客观形色的局限,加之传统绘画的象征与符号性质,线、色、形都是情感与精神的符号,当仰韶文化的原始先民和青铜时代的人们把他们所崇拜的动物、植物乃至天地山河抽象、符号化为某些规范图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如以今天所称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或“适合纹样”等等手法平面地组合排列时,它们就已经具备了今天我们所称的“图案”的“装饰”的性质。同时,中国的色彩更从山顶洞人时期就具备分明的象征性质,而每一部落,每一时代、每一方位几乎都有自己的固有的象征的色彩种类,而不论是东方早期的“五色”抑或是老庄“五色令人目盲”的反色彩和后世的因此及“道”的观念而来的水墨现象,则都是同出于东方观念象征的超自然思维之使然。同时,人类早期艺术中经常使用的造型用线也因超自然和虚拟性而愈发精炼而完美,其虚拟、抽象和超现实的特点,则和前述同样超现实的形与色一起,共同形成具浓郁东方文化象征内蕴的今天人们所称的“装饰”性特色。
与上述特征相关的还有综合性特征。由于传统绘画对精神情感的象征与表现性能的高度强调,中国画家根本无需刻意再现。故受自然客观规定性之束缚较少,这就给在抽象性平面性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加之符号表意性本身的单纯性与符号间组合性表意特征的需要,中国传统绘画一直具有“综合性”的特性。不论是在原始艺术时期就有的“龙”是对多种动物的综合,以后的凤、麒麟,也是综合的结果;就连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的伏羲与女娲,也是人首蛇(龙)身的综合性的产物。这种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形象从仰韶文化彩陶纹样开始,一直到汉代画像砖上可谓比比皆是。当然,最典型的综合性应属文人画中的诗、书、画、印的结合了。这类多种手段的综合利用非但因传统绘画的上述性质而不会碍事,反而会因多种手段多种功能的综合传达而相得益彰,所谓“画之不足题以发之”是也。诗、书、画、印的综合运用的确也成为中国绘画独树一帜的重要特色,这也是“综合性”特性之使然。
(作者系四川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