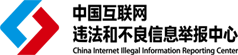重燃的星火
□李文汉
1996年暮春,我到昭通机场看望从事飞播的同志。在获得机组的首肯,我乘坐飞机经石门坎上空从捡角寨、摩娥进入马尿河河谷,机舱内的同志解开袋装的松子倒进飞播装置,松子匀净地散往地面。飞机顺着河畔斜坡飞到白岩脚,绕到画眉梁子,在狭长的河谷上空兜了几个圈。
我透过机窗,在牛脊似的大青山上,看见一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周边村民带着食物,披星戴月聚集在山顶,看着盘绕在河畔的飞机欢呼跳跃。
马尿河畔连绵密集的原生态植被,约在明、清时期,人类的足迹踏入之后,选择西边岩头台地和河谷偏坡筑建了几个稀疏村落,辛勤开垦荒地,种植低产作物,过着“刀耕火种”、“坐山吃山”的安静生活。承继着传统的信仰,有的村寨保护着一座树木葱翠的祭山,有的在坟山种植树木,为祖辈安身遮风挡雨,因此,山林苍劲,树影婆娑。河畔密林深处躲着虎、豹、野猪、黄麂,峭壁里栖息着麂、青麂和猴子,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数百年的成片山林,随着一阵阵斧头砍伐声和滚滚的浓烟,马尿河畔的栓皮树、青树惨遭砍伐。
飞机轰鸣盘旋,我仿佛误入一个陌生地。故乡两则故事从我脑海里涌出。马尿河一个村庄的两父子擅长狩猎,在一个雪花飘飞的夜里,他们点着麻杆到房背后的树林打箐鸡,精狡的箐鸡站在树枝,借着微弱的火光隐约看见松叶里的箐鸡,当他们拉弓搭箭,树林深入射出两道蓝莹莹的光。顿时,他们被吓得连滚带爬回来,掀开门踉跄进家,迅速用门杠抵住,浑身打着战栗。
马尿河沟壑像肋巴骨,森林成片,箐林很深。寒冬的雪凌给两岸披上银装,寨里狩猎的人走到岩口就留下年小的站在岩口看哨指点。每天早晚鹿子要到河边喝水,猎人顺着脚迹找去,猎狗嗅着气味钻进林子把麂子吓出来,铺天盖地的雪凌,猎狗在树窟窿中追着麂子。猎人只能寻着狗的狂吠声判断猎物的去向。看哨指点的人看不见猎物的行踪,站着搔痒摸出一只虱子搁在手巴掌上,看着虱子爬行的轨迹,大声指使猎人追撵麂子。猎狗的狂吠声越来越远,猎人们被蒙在鼓里,还在杉树箐跑来跑去。
我目睹窗外已经不是树木葱郁,野物栖身的地方,马尿河的生态植被出现严重的失衡和危机。
故乡人曾忧心如焚地告诉我。那几年,河边肋骨般的溪沟水断流,沼泽湿地干裂,奔流不息的河水流量递减。稀有的白皮柳树和海棠树在这种气候下变得渐渐枯死。山林里的野猪、麂子突然迁往他处,野猫、狗獾、白面狸不见踪影。生态的失衡和危机导致春夏炎热雨水稀少,冬季干燥雪凌难见。这种显象和潜在的危害当地的人们都有感觉。大青山上人们对飞播欢声雀跃,不完全是看飞播和凑热闹,它透视出人们在心灵深处对现实生存生活的环境感觉出了问题。
那次飞播,大家对恢复河畔的生态植被看到了希望。不久,山林间小路、山口、梁子竖起醒目的木牌,上面写着“禁止人们带火进山,禁止人们随意放牧,禁止人们盗砍山林”。禁令如同紧箍咒锁定飞播地方。雇佣的护林人员腰间别着月牙形的镰刀,林间的小路变成巡察小道。对严格的禁令和封山,有的人还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竟然闯在“刀锋上”。王老表在一个牛毛细雨天在河边砍了一背柴,被巡察人员逮着,毫无客气地对他说:“我们都是早不见晚见的人,对不起要罚款五十元。”王老表知道错了,叽叽咕咕地回答:“你听说农民进山揣钱吗?”巡察人员说:“不要你现在交,三天内把罚款交到护林办公室。”王老表被罚,他很难启齿,可是纸包不住火,这件事还是传开了。
飞播的黄松因春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张狂,播下的松种在气流的作用下,一粒粒松子飘落在山林或溪沟边,幼松长起来有的密集有的稀疏,在栓皮树、青树的遮护下,幼松把根扎进腐质土里长起来,没有松树的地方,得益于封山护林,各种树木攀附长高。
生态植被的修复传到我的耳廓,回去看看鼓鼓劲对故乡人有益无害。
那天晚上,王老表的家围坐着当年的同班等辈,他把我当作贵客,宰了一只羯羊。饭后,他拿出长辈待客的那只被搓摩得发亮的岩羊角斟满酒递给我,我双手接着轻轻斜倒沾湿嘴唇就递出去。在座的人起哄起来,说我已经瞧不起他们了,我受不了这种激将的话,举起岩羊角酒一口吞完,并迅速将羊角搁在衣包里。王老表心知肚明,又拿出一个碗斟起满当当的酒。我端着品了一口就递出去。大家把我拉进去喝“转转酒”。有这么多的同班等辈,王老表感到很体面,他喝了几转,兴致就高起来。在座的人嘲笑他已经赚五十元,王老表对他们说,“你们错了,主不吃,客不饮。喝酒赚了五十元,何止这个数。我赚多了,而且你们人人都有份。”这句话在座的可能没有一人听懂。他挨近我悄悄地说:“明天到马尿河看看当年我们捡柴和打猎的足迹。”
蛇形般的马尿河,河畔边的马桑树林被毁挖成了地,狂风暴雨袭来,漏斗型的河床盈满激流,在拐弯的地方洪流像脱缰野马狂奔,撕开一条新河道。新桥那片一百多年的杉树是高家祖坟树,据说家族在保护和砍伐的争执中,达成保护的共识,但隔夜突然变卦,杉树林毁坏在晚辈手中,粗壮的根部都被挖走。残存的根须淌着泪滴般的杉油,十几座坟躺在光秃秃的山洼里。我们走到沼泽地,站在当年放牧烧着大火烤洋芋、包谷吃的小山顶看,密林深处的溪沟无声,明镜般闪烁的沼泽地干枯开裂……
我的心隐隐发痛,期待和想象与眼见往往有距离。我低着头,几幅原来的生态植被从心中跳出来。马尿河畔是长条形的冲积平地,泥土之下是一层沙土和鹅卵石。河水流淌碰到成堆的鹅卵石就绕开,留下的半岛长出成片密集的马桑林,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鱼洞对面杉树林,密密匝匝的映山红灌木让人钻不进去。是麂子和箐鸡安身的宝地。麂子出没在附近人家的蔬菜和麦苗地里,箐鸡在屋后同鸡抢食吃。那片沼泽地溪沟流水潺潺。沼泽是陷阱,我曾多次领教过,牛身强体壮,只要用力牵着尾巴,慢慢地助力,牛会凭借躯体的力挣爬出来。马脚力好,陷入沼泽,周身发抖,四脚乱踢乱刨,越陷越深,最佳方法是用木棒撬开肚子下的软土,用抬杠帮助脱离险情。
王老表低着头不说话。我能责怪他吗?他怀着一副热乎乎的心肠,带我看当年捡柴和打猎的足迹,多么诚恳的心啊!时过境迁,曾经留下是脚迹的地方经过封山护林之后,重新长的树已经蓬勃生机。要知道,马尿河畔除了那几片人为毁坏难以恢复的地方,幼树已成林成片。想起飞播的哪几年,河畔的人们舍小家顾大家,王老表就流着眼泪卖完了一群羊,很多人家淌着眼泪牵着牛马到集市场。他们熬了几年苦日子换来这片山林。
我们走到野猪箐、眉头箐眺望,混交的阔叶树、针叶树齐刷刷长有楼层高,我仿佛置身于无边无垠的碧海里。正值树叶初发,花蕾绽放,山林深处一簇簇映山红张开着火焰似的花,小巧精明的太阳鸟在花丛中缀吸着甜蜜的花露水。衣着华丽的雄箐鸡翘着长尾,“阔阔阔”地鸣叫,后面紧跟着一群“妻妾”。
我掏出香烟发给他们。王老表提醒说:“抽烟得当心。一旦惹起山火,那不是五十元,人都要拍出去。”他憋着的气消了,充满信心说:“老祖辈留给我们的青山绿水在一两代人手中毁了。我们要像护神山树保住马尿河的生态植被。”我想,老祖辈留下的生态植被是生活所迫,他们过去躲在山林,吃在山林,以山林为家留下来的,复原当年的生态植被,要有“百年树木”的眼光。王老表望着我对他那番表明决心的话没有回应,很失望地看着我。我对他说:“恢复生态植被,大家功不可没,已经十拿九稳。要复原老祖辈留下的植被、沼泽地和沟边几百年的古树咋办?”王老表听后问我:“那么,我们子孙后代能不能进山林捡柴和打猎?”他喉咙突然被噎住,不再往下说。我告诉他:“捡柴会成败家子,打猎就是伤天害理。你可以过‘坐山吃山’的日子。”他听不懂,催着问:“快把肚子的话掏出来讲,烂在肚子里可惜。”我停了一阵后就说:“我说的话不一定对,坐山吃山要靠你们去摸索。像这片山林,用不着几年,有了成群的野猪、麂子、箐鸡,树下跑的,树上飞的,食物链拉长了就是上苍赐予的财富。马尿河就成了生物聚集之地。那时候你不要捉只虫子放在手心上忽悠外来的游客。”
王老表听后问我:“你说我们护这片林子就是为了这些吗?”我说“就是为了这些。这里面的价值是生态的,又是经济的。生态的价值就是调节气候,使河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经济的价值在于树林本身。树本、草本寄生草,需要下功夫去识别。夏秋之间各类菌子、山沟的野生猕猴桃、四照花的果、毛栗子……还可以在箐林租出一块地,养寨子里精心保留的茶花鸡,发财的门道多着呢!”
王老表露出掉了门牙的嘴,笑得合不拢嘴。他说:“我从电视里看见那些从事农家乐,搞乡村旅游的地方,客人像蚂蚁一串串来,又像散食喂鸡一样,主人将大把大把票子装进腰兜里。相比之下,我们有自己的强项,除了吃山珍外,可以导游客人看岩上的野鹿、青麂、黑麂。在山林撵箐鸡、追松鼠,还可以教他们用蝗虫作引子找马蜂巢,在马尿河摸那些躲在石块的鱼……”
故乡马尿河生态植被星火,点燃了故乡人的生活梦,开启了故乡人的心扉。他们坚守马尿河畔几百年,保住这片箐林就是保住原生态的生活,赏青山之靓,饮绿水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