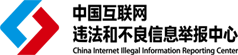爱种树的父亲
□汪秀红
中老年朋友被称为银发一族,感觉自己越老越活成老顽童,小孩子的特点在于看见别人吃东西他会盯着看,因为想吃。
我现在也像老顽童,经常想像儿时一样和小伙伴一起疯玩。记得一次在小伙伴家,看见他家有一篮桃子放着,我们站着不动只是看,小伙伴的家长就笑着说,想吃是不是,把桃子像滚保龄球一样滚到面前,吃了却觉得味道不对劲。
再后来我家后院种了很多桃树,父亲是种树能手,喜欢种植果树——柿子树、桃树、梨树、李子树、石榴树。记得院子里有棵柿子树,是我五岁那年种下的。我等了一年又一年,柿子树都没结出柿子,我想放弃,奇怪地问父亲为什么不种葡萄或者别的,父亲只是看了我一眼,又扭转头看着枝叶葱茏的柿子树笑说:“别急,你得等它慢慢长大。”几年过去我几乎忘了这棵不结果的树,直到那年,柿子突然变成餐桌美食,我才诧异其隐忍。自此,童年生活的餐桌上都离不开柿子。每年,父亲都把柿子晒干成柿饼,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配红薯等,变成我们餐桌上的美食,那种甘甜的味道,不用吃就已甜在心里。直到父亲离世,我离开故乡,现今一头银发,柿子树依然坚守,陪伴着父亲的思念。看着眼前默立的柿子树和院子苍苍,心中渐次开朗起来。夏天青翠的山,正收获着宽阔和深远,经历了严寒酷暑的柿子树,也正平和地迎接着生命靓丽的色彩。冷与暖,清远和安详融合走进彼此生命。
记得以前房墙刷大字白色标语:“房前屋后种桑种树。”我家的后院被树包围着,前是柿子树桃树后桂花,左边樟树右李子。父亲很有办法,他不知从哪弄到树苗嫁接。只见他一把篾刀纵剖树心,把削尖的苗子移植在树上,缠上层层白胶带,施了肥树就疯长。桃树从四月桃到十二月桃都有,以前担心桃树不结果,后来担心结太多吃不完,索性送人,再后来父亲说你们不在家不想送人,就让果子落地里。有年回家,我看着桃树不像以前繁茂,桃树被整饬干净,就像刮过胡子修过面的男人一样清爽,结的果越来越小,树底杂草乱生。父亲去世前,已弄不动他盘来的这些树,全部砍了当成柴。我说好好的树砍了可惜,我知道如果不是兄弟姐妹一直读书,他缺少人陪伴,也不会砍这些树。
父亲去世前一年精神不好,拿起工具说要移栽桂花树。这棵树模样中正,形状很好,像许愿树。这棵树我们挖了很久,因为挖树必须带土才能活,我们在它周边开挖,挖了一个上午,挖好之后用绳子把根须包好。最后连土带树约二百余斤,抬到屋后种下又花了个把小时。如果这棵树他挖得动,他肯定不会叫我,因为他病了。夏天,树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不会觉得热,我乘凉就把竹床搬到树底下,舒服睡个午觉。想吃果子随便摘,不用洗,擦擦就吃。我写作业把小桌子抬到树下,慢慢写慢慢想,直到天黑。我如果背书背不出,抬头看叶,静静,就能背得出,欧阳修那篇《秋声赋》就是在樟树下背完的。那棵树下曾趴着我养的猫,还有一本放在树杈上的古文选,还有父亲喊我吃饭的声音。
父亲砍树是对的,因为后来他去世了,树在人不在,没人修剪没人打理,看着心里难受。彻底没了反而一身轻松,斩断联系牵挂就空了。他说如果哪一天他不在了,就把他葬在他修剪的树下,但他提前砍了树。我后来腿疼,坐在桃树底下歇了很久,凉快忘记疼,忘记痛,这或许就是像我这样的中老年朋友银发一族和树的心声。最终,我没把父亲放在他修剪的树下,却放在佛寺的盒子里,没能如他的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