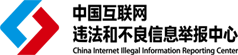给 母 亲 取 名
□唐子华
母亲的生命定格在她82岁那年的一个雨夜。我对母亲的思念,亦如那一夜的雨丝,绵延不绝。
母亲出身贫寒,从小未进过一天学堂,因而也不曾取过书名。嫁给父亲后,村里人按当地习惯,将父亲的姓和她的姓连在一起称“唐莫氏”。直到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报名表上需要填写父母的信息,母亲姓名一栏难住了我。母亲虽无书名,乳名还是有的,其中一个字是“垠”。我查新华字典得知,“垠”是心胸宽广的意思。加上母亲在娘家是“秀”字辈,我便给她取了个书名,叫“莫秀垠”。“秀”有清秀、秀丽之意,放在母亲身上,还可理解为心地善良。“秀”“垠”组合,是个蛮有意思的名字。我把我给母亲取的名字告诉她,并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给她听,她很满意。于是,母亲自此有了属于自己的书名。
我觉得母亲的一生,正如我给她取的名字:心地善良,胸怀宽广。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脾气温和,说话轻言细语,打从我记事起,从未见她与父亲吵过嘴,也从未和村里人红过脸。
外公去世早,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外婆住到了县城小姨家。暑假里,母亲带我去小姨家看望外婆。从老家到县城,要走30多公里的路。因为没钱坐车,11岁的我跟着母亲一大早从老家出发,爬坡下坎,过河跨沟,走得气喘吁吁。走累了我不想再走了,母亲过来替我擦去脸上的汗水,鼓励我说:“快到了,再加把劲。”快到城郊的时候,母亲却叫我在路边等着,她要到树林里去一下。不一会儿,母亲扛了一大梱柴禾出来。她说,我们家穷,来小姨家看外婆都没带什么礼物,我顺便给她们拾梱柴禾,也算没有空着手来。
上初中的时候,我要到乡中学去寄读,母亲叮嘱我:“儿啊, 人穷志不穷,山穷水不穷,平时穿衣服要穿干净哈!”我一直把母亲的话记在心上,不管衣服怎样旧,都会洗得干干净净。
有一回,我从学校回家,感觉全身不舒服,就躺到床上昏睡。干活回来的母亲看到后,马上明白是“出麻疹”了。她趴在床边,心疼地摸摸我的额头,又仔细查看我的肚子和背上,看到麻疹出来了,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听到母亲问话:“幺儿,想吃哪样,妈帮你做。”我随口说了句“妈,我想吃甜酒粑。”接着继续昏睡。
一觉醒来,母亲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甜酒粑端到我面前。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我没有听到家里的粑槽响,也没有看到家里有红糖,更没有看到家里有甜酒啊,这碗甜酒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母亲告诉我,粑粑是用粑棒冲的,甜酒是用饭做的。红糖是怎么来的,我就没有记忆了。依稀记得,吃下一碗香喷喷的甜酒粑,我的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那一刻,我感动得眼里噙满了泪花。
我首次参加高考失利,母亲没有埋怨,而是鼓励我不要放弃。她说:“穷人家要喂猪,男孩子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息。”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也同意让我复读,并把家里一棵粗壮的杉木树卖掉,给我交了补习费。功夫不负有心人,再次参加高考,我终于榜上有名。后来,还成了一名国家干部。我常想,如果没有母亲的坚持,没有父亲的理解,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想着这些,倍感父母的伟大!
参加工作后,我先是在乡镇,后又辗转罗甸、平塘、都匀等地。平时工作忙,回家看望父母的时间非常难得。但只要一回去,母亲定然开心不已。有一年,我带着妻儿回家过年,哥嫂、侄儿侄女们,全家15口人,喜乐融融地围绕在父母身边,与父母一起拍了张全家福。我在罗甸工作的时候,不再为生活操劳的母亲有时也会离开老家,到县城和我们居住。但也许是操劳惯了,母亲总是闲不下来,她每天都去菜场买菜,帮我们做饭,料理家务,不让我们操心。我在都匀安定下来后,母亲也跟着我们到都匀住了一些日子,依旧不改勤劳的习惯。刚开始,由于对周围环境不熟悉,母亲就让妻子陪着她上菜场、走商场,熟悉了就自己去了。并很快熟悉微波炉、电磁炉等家用电器的使用。我们一上班,母亲就在家擦桌椅、拖地、打扫卫生,买菜做饭等着我们回来。
母亲80岁那年,我们陪她回老家过春节。为了圆她的“火车梦”,我们特意绕路,从都匀坐火车卧铺到独山,再从独山乘汽车回罗甸。买好票后,我牵着母亲的手上了火车。母亲特别高兴,一路上感觉十分新奇。她说:“在电视上看到火车好长,现在坐上了,才知道车上还有床,坐起很稳,不晕车。”
……
往事历历,那个雨夜的戚戚悲声犹在耳际。
不知不觉间,母亲已去世13年,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已发生变化。但母亲音容宛在,我对母亲的思念一刻不曾减。
母亲的深恩我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