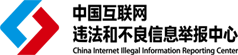老 屋 趣 事
□朱克乾
孩提时候,老屋并不孤单和寂寞,这就是值得我怀念的理由。
在我七岁之前,老屋前面是一块菜园。园内有三棵大的杏树、李树和梨树,还有几棵小的杏树、花红、石榴。弟弟妹妹们小,我是长兄,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母亲带着我给这些果树喂饭,母亲用蔑刀在果树主干上砍一刀问一句,我回答一句,完毕,母亲从我端着的饭碗中抓小撮饭喂到果树上被刀砍成的口子里。果树开花了,慢慢的凋谢,再经过风吹雨打,果树们把结出的果实当成自己心爱的儿女紧紧地抱住,再经过两三个月的坚持,不辜负母亲的心,果子结的很厚,母亲摘下来,我们一家人尽情地享受,同时也给邻居家的小朋友们分享。
果树一年年长大,枝丫繁茂,春天到来,树叶一个劲的比拼,枝丫也在叶片的强取豪夺中争抢空间,卯足劲伸长,茂密起来,成了鸟雀们的天地。叽叽喳喳地争论不休、成双成对地打打闹闹、在枝丫与地面间忽上忽下、或在枝丫间跳来跳去、在这棵果树与那棵果树间来来往往。还有的谈情说爱,把这儿当成了它们的伊甸园,筑窝建巢。有一对非常美丽的鸟,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画眉那么大,雄鸟全身洁白,有两羽孔雀尾那么长的羽毛,雌鸟全身赤黄,短尾巴。它们衔来背阴处的小草筑在巢的外面,细小柔软的干草筑在巢的里面,巢就筑在一棵小杏树的双叉上,离地面一人高,好像根本就不怕有人打扰它们的生活,也不怕会有人伤害它们的后代。我很好奇,搬一条凳子放在杏树下面,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尖,够着身子伸长脖颈看它们孵化的小蛋,用小手摸摸,拿在手上瞧瞧。听大人们说,人摸过后有气味,蛇就会闻着气味而来,有一个绝招,只要放一根头发在巢里,那蛇就不敢来了。每次摸了我都会这样做,还真灵,小鸟顺利地孵化出来,并顺利地长大,展开翅膀飞出暖融融的巣,寻找自由的天空。
果园里虽然果树枝丫茂密,但通过叶与叶之间的缝隙,还能透出一些阳光和雨露。春天到来,母亲翻开果树下面的泥土,种上几窝南瓜。南瓜不挑拣土壤的肥瘦,有泥土就能生长,在每一个发叶柄的地方,会长出白嫩嫩的锥子,一旦插入土壤就生成细小的根,吸收地下的养分,这大概是南瓜不怕贫瘠的缘故吧。南瓜生长繁茂了,把老一点的叶和柄一起割下喂猪,减轻了我们到外面去割猪草的负担,为我和弟弟妹妹们腾出时间来安心学习完成作业。开花了,有很多雄性的花,母亲把花摘些来,放入用鸡蛋调和的面粉里给我们煎炸了做菜吃。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吃一回肉都被称之为打牙祭,油炸的南瓜花也是一道多么美味的佳肴啊!干吃香酥,煮汤柔滑细腻。小时候,最喜欢吃母亲炸的南瓜花。父亲买来猪肉,剁成肉末,母亲摘一个小碗那么大的小南瓜,去掉中间的瓤,把肉末放在里面,加些佐料蒸来吃,那又是一道绝美的佳肴。
果树长大了,我和弟弟妹妹们也长大了,需要活动的场所,菜园里不种菜了,改成了院坝。特别是那棵一围多粗的梨树,不知是什么时候就从双叉处把枝丫砍掉了,只剩下一人多高的树桩。但还活着,每年都要发几枝嫩枝条,显示出勃勃生机。这节树桩却充当了我小时候最好的伙伴。找来一节八号铁丝,钉在树桩上,成为篮圈,当然,树桩就充当了篮板,我和小伙伴们玩皮球,在树桩上投篮,无论我们怎样砸,梨树桩都没有怨言,不像学校的破木篮板叽叽歪歪的发牢骚,还颤颤悠悠的吓人。篮圈掉了又钉上去,掉了又钉上去,反反复复,树桩被我钉出了很多伤疤。皮球砸重了,时间长了,被砸过的地方会掉下一层皮,露出白黄白黄的韧。我得到的快乐越多,梨树桩付出的痛苦越多。但也正是那一段老屋生活的旧时光,给我的童年带来了难以忘怀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