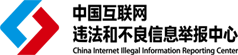魂响沙梁
□傅俊珂
沙烫脚!火烧云!敦煌城在身后逐渐变成个小黑点儿,戈壁就狞笑着扑过来了——鸣沙山,到了。
沙丘金浪,直涌到天尽头。日头毒,烤得沙脊起青烟,烫得空气直哆嗦。瞧那沙梁上,驼队排到天边边。一峰峰骆驼,驮着花花绿绿的游客,慢悠悠,慢悠悠,踩着滚烫的沙粒,齐刷刷往前挪。铃声悠悠荡开,脆生生,钻进我的耳窝窝,在血脉里打起转转。姑娘们彩衣飘飘,纱带子缠胳膊绕腿,风一撩,便似要飞天。风不来,摄影师急得跺脚:“等,等那口气!”忽地沙粒横飞,裙裾乱卷,姑娘慌忙去按,抬眼却撞见同伴眸子里的火星子。那光掺着烈日,把沙丘上的人影,霎时熔成了洞窟壁画上飘下来的仙。
我的魂,叫那驼铃勾走了。叮当,叮当,一步一叩。驼峰高耸,投下长影在沙坡上爬——影比真身还驼,浓得化不开,像另一个活物贴着沙丘蠕动。可惜啊,天眼(无人机)在这儿是哑巴。俺只能端着相机追着看:这峰刚卸下客,汗珠子还没渗进厚毛,下一拨人已猴急地攀上鞍。长队望不到头……沙窝子里的热浪裹着牲畜粗重的喘息,喷在干燥的空气里。
高高的山丘上,早已挤满了人。红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老远看,那晃动的人群,像成千上万只小蚂蚁。游客脚上的红色防沙鞋套,也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日头西坠,烫劲儿稍褪,我们才往沙山顶上拱。软梯?早叫人墙堵死。那就手脚并用吧。沙吃脚,腿灌铅,陷一步,溜半尺,肺要炸!沙粒钻进鞋帮帮,硌得脚底板板生疼。当年巴丹吉林的重装徒步,十五里沙海翻浪如履平地——如今?沙山欺老,岁月这把钝刀子,悄悄割着我的气力。
终于踞立沙山之巅——西天正泼着赭红的火。晚霞漫过沙脊,凝固的沙浪成了熔化的琥珀。风的手指拂过,刻下细密纹路,那是大漠的年轮,在残照里幽幽放光。俯瞰下去,月牙泉静静卧在沙的臂弯里,绿得心惊,像谁遗落沙海的一块翡翠。沙环抱着水,糙砺依偎着柔润,天造地设的痴缠。
沙梁下,驼队依旧蜿蜒游动,铃声碎在风里,叮叮当当,牵着千年前的商队魂灵,直送到俺耳边。这一汪水,沙暴千年吞它不下——原来底下藏着粗砂层,暗涌如脉。党河与大泉河,一东一西,扇状洪积如母亲张开的臂膀,将这弯清波稳稳托在掌心。水自西南悄悄渗出,东南又默默渗回地腹,沙与水,在此订下亘古誓约。
暮色四合,沙丘敛了炽金,披上紫灰的袍子。泉边灯珠次第亮起,水波漾着光,真似月落沙海。
骤然,一道沉浑如古钟的声浪炸开——“敦煌的夜,是千年的眼睁开!” 主持人立在沙海中央的舞台上,声线裹着磁石,每个字都往人骨缝里钻。话音未落,山坡上“唰”地亮起一片星海。荧光棒活了,黄的、蓝的、绿的、紫的,在起伏的沙谷间游动,汇成光的河流,绕着沙山脊线蜿蜒流淌。歌声起来了,不是独唱,是万人胸腔里滚出的雷。这山刚吼罢“大漠孤烟直”,那坡就接上“长河落日圆”,声浪撞在沙壁上,反弹回来,嗡嗡地响。忽见对面陡峭的沙坡上,红黄的光束游走,巨大的歌词被斜斜地烙在山体上——“羌笛何须怨杨柳”。字迹在沙的皱褶里扭曲变形,像古烽燧燃起的狼烟信号,灼痛了仰望的眼。
就在这声浪灼灼、光海翻腾的当口,西天残存的火种彻底点燃了。赤焰翻滚。橙流奔涌。青紫色的云絮被镶上金边,天穹成了倾倒的琉璃窑,熔化的彩釉肆意泼洒。月牙泉的水面,霎时盛满了这魔幻的光谱,绿波里跃动着赤橙黄绿,宛如打翻的众神调色盘。整个鸣沙山,从沙粒到每个人的发梢,都浸在这流光里,分不清是人间幻境,还是天宫倾泻的琉璃火。
蓦地,夜空深处传来蜂群振翅般的嗡鸣!千百只光点从沙海四周升起,悬停于墨蓝天幕。嗡——嗡——光点开始游走,聚拢,散开。一峰光塑的骆驼昂首阔步,驼铃声仿佛穿透虚空从千年前传来;倏忽间,驼影碎成星屑,星屑又旋舞重组,一尊衣袂飘飘的飞天凌空舒展,璎珞流转,长带当风,比莫高窟壁画上的更灵动飘逸。人群的惊呼还未落下,光点再次变幻,交织成巨大的、繁复的藻井图案,穹顶般笼罩四野——那是佛国的华盖,自千年石窟飞升,罩住了今夜沸腾的沙海。一万七千双眼睛似被钉在夜空,魂魄早已出窍,追着那光的驼铃、飞天的飘带、佛国的穹顶,在星子间浮沉游荡。
夜已深,喧嚣未歇。手机电筒在沙坡上明明灭灭,汇成倒流的星雨。灯光变幻如妖,歌词竟被打到对面山体上,巨大,红黄。归途中回望,鸣沙山与月牙泉已融成一片深幽的影,宛如静卧的远古巨灵,怀抱千年沧桑,不言不语。只有风过沙鸣,低沉呜咽,成为大漠胸腔里永不消散的一声叹息。
沙山抱月是痴情,泉水映天是守诺。莫高窟的微笑未老,古道驼铃散了又聚。可这沙泉吻,壁画笑,古道驼铃叮当响……早化成了魂,烙在我的心板板上。沙是干的河,泉是月的泪,千年的相守,磨亮了敦煌的魂。
敦煌,别了!那铃声,真的咬住我的魂,怕是一世也挣不脱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