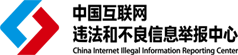苏轼的书房
□董全云
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有一来凤轩。苏轼的《梦南轩》写道:“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南轩,是苏轼和弟弟苏辙小时候的书房,后来被父亲苏洵改名为“来凤轩”。
歇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正面左右两侧各开一方门,通连室外风雨廊;中开一圆门,上方悬“来凤轩”匾额,两边“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楹联。南轩连廊回绕,青砖铺地,铁树亭亭如盖,数株青竹簌簌。房子和院子背靠几株高大桢楠,显得古朴静谧。
苏轼自谓平生最快乐之事就是读书,“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南宋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写他的家乡眉山,“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两宋三百年间竟出了九百进士。
苏轼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子由韵二首》中写南轩的景致,“竹柏杂花,丛生满庭”“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足见南轩是东坡先生的诗意栖居和精神乐园,也是他青春时代的美好回忆。
晚年,苏东坡在《夜梦》中回忆起当年在南轩读书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在南轩,慈母程氏“亲授以书”,教育苏家兄弟不发宿藏、不残鸟雀,带着他们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听完后问母亲:“如果我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会同意吗?”程氏回答:“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为了“义”,儿子可以奋然舍身赴死,母亲可以慨然牺牲骨肉。此种大义从母亲流淌至儿子,从儿子回溯至母亲,唤起的正是苏轼藏在体内、寓于寻常、塞乎天地的生命元气。
多年之后,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诬陷下狱,囚于御史台,看到风吹乱庭前的竹子,他便写下“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竹子可折不可辱,风停了后又重新站直。在这首诗中,他又提到“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在最无助最艰难的生命境遇里,南轩是他的精神家园。可见,少年时的一间书房,对涵养东坡先生的君子品格是何其重要。
后来,苏轼又以“讥讽政事”被定罪,诏贬黄州。到了黄州,没吃的,“问人乞米”;没住的,寓定惠院,客临皋亭;没朋友,“深自闭塞”“焚香默坐”。从志在天下到自身难保,“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生命似乎走到了绝境。
“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人生让苏轼对书房充满渴望。他在东坡筑堂,将正中一间作为书房。房屋落成时适遇大雪,他便将房内四壁均画上雪,命名为“雪堂”:“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雪堂虽简陋,却造就了苏轼安放身心的居所。
在雪堂,他起居偃仰,隐几昼瞑,栩然自得,“真得其所居者也”。但“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欲为散人而未得”。“东坡之胁,筑而垣之”,围墙筑舍是他微弱的个体生命之需,但“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有色之雪有形之堂又成为了五官之害,内心之蔽,欲静不得,欲逃不能。在“入”与“出”之间,在入不进、出不来之间,他最终选择了“适意”,选择“无邪”,“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让雪凄凛肌肤,洗涤烦郁,让八荒之趣尽在眉睫之间,让生命随群息而动,随大明而升,与万物同生,与山川共美。
北宋绍圣元年(1094),已近花甲的苏轼再遭贬谪。在惠州的白鹤峰上,他又建了自己的新居,书房名之“思无邪斋”,并作《思无邪斋铭》:“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圆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不管命运多背逆,生活多无常,处境多糟糕,苏轼一直不放弃建“书房”。黄州“雪堂”没了,惠州建“思无邪斋”;“思无邪斋”没了,海南建“桄榔庵”。无论身在朝堂,抑或在江湖,有了一隅书房,他能在“深自省察”“摄心正念”中打开另一条生命的通道,因为“无身”所以“无病”,因为“廓然”所以“圆明”,因为“浩然”所以“我正”。
从少年南轩的“奋厉”到中年雪堂的“适意”,再到晚年惠州的“无邪”,无论漂泊到何处,书房总是他安顿身心的精神寓所。有了一隅书房,苏东坡沉淀出世事沧桑都染不了的那份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