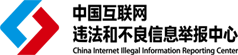我们曾经认真执行过“前十条”和“后十条”
——我的一段“四清”经历
□龙志毅
我曾经有过参与执行“前十条”和“后十条”的“四清”经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实将它记录下来,也许对研究那些年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对青年一代也有认识价值。
那时的前十条和后十条,在我们眼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中央先制定了前十条,经过试验和调研,又制定了后十条加以完善。感觉的是:四清已由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的经济型转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的政治型。也就是说“四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我不清楚那次全省组建了多少“四清”工作团,只知道党群系统外加公安厅,抽调了几百人去惠水,团长是时任省委党校的副校长冯玉理。党校的体制是由一位分管组织的副书记或组织部长兼任党校校长。日常工作由常驻党校的专职副校长主持,冯玉理就是省委党校的实际负责人。那时党校已停课,全力搞“四清”。
这个团由党群系统和公安厅抽调若干人组成。团省委共去五人,有我和刘兴邦、周日新,其余两人似乎是朱梦侠和罗漫南?记不清了。我当时为团省委办公室副主任,自然成了五人的领队。因参加团省委常委扩大会研究当年工作,我晚报到了一天,然后在第二或第三天,同组织部同样晚报到的七八个同志一起,乘一辆大卡车赶去。消息传来,工作团已去摆金,我们便直奔摆金。时值春节刚过,那年冬春特别冷,只见沿途的树枝已经挂上了冰凌。我们到达时工作团已正式分工,我和刘兴邦去甲烈公社,其余三人均分散参加各组。组织部的处长高守明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县里也抽两人参加。其中老石为县监委专职委员,他也明确为副组长之一。我和老高分工,他年纪大(约四十左右)坐镇甲烈片五个大队。我去约十里外的摆王片,抓五个大队的四清。
工作开始时,面对的是召开动员大会,但下了通知没人来。工作组和公社干部连夜冒着零下四度的寒冷去挨家挨户动员,第二天,总算来了一百多人,便开了一个动员会,算是“师出有名”。
我去的摆王片,以摆王寨大队为重点,指导其它四个大队的四清工作。摆王大队约一百来户四五百人,分几个生产队记不清了。我在摆王大队执行的是搞运动的老套路:回忆对比,以提高觉悟;摆现象、查敌情,以搞阶级斗争;然后转入内部清政治、清思想等等。和往次不同的是,这次一开始便组织贫下中农筹委会,明确依靠对象,拉开阶级阵线。为了摸清阶级阵线的底,在回忆对比阶段,开了个积极分子会,分析了全大队以人为对象的“保密”会议。除明码标价的四类份子外,有各种各样“问题”的竟占30%。虽说是“秘密”,消息却迅速传到这些人的耳朵里,使他们终日坐卧不安。其实不就是一些一般的历史问题,如当过甲长、一般土匪、保丁等等。
1964年2月29日,我曾有过一段日记。现在先将它如实抄录如下:运动开展以来,社会上已引起强烈震动。贫农兴高采烈的说:“分的房子住得长久了。”中农有些发慌,四类分子更加恐惧,到处讨好,见人就打躬。还有些有历史问题者也跟着慌张,要求“宽谅”。这是听汇报的记录,有虚有实。各类人员的恐慌,确实存在。至于贫农兴高采烈……,那一段话倒也未必。我的房东就是贫农,他家的房子也是土改时分的,我每天同他的接触摆谈中,并没有房子住得长久了的感觉。过“四月八”时,他按习惯打带颜色糯米粑,还特地给我拿了一块热毛巾以便擦手,日子过得挺舒坦的。我走访过的贫农不下二三十户,也未听到共产党的天下坐不牢,地主要“翻身”的语言。怎么汇报时又冒出上述一句呢?这是运动语言。有的生产队长为了迎合上级,如此而已。接下来便是“察敌情,摆现象,搞对敌斗争。”布依族的寨子,特点是中农多,地主也有那么几户。其中有这么一二户地主,劳力强,土改后日子还可以,但人缘不好,几乎每次摆敌情,都有他们二人的份。
那时还是冬春之交,天气严寒,有时结冰。我免不了三天两头去甲烈“组部”碰头。虽说十来里路却也要翻山越岭,当时三十出头,气饱力壮,竟将它作为景观大作其诗:
大地化银河,群山翻作浪。
谷底冰柱立,冰峰奇花放。
我在浪中行,脚下依稀晃。
围炉虽云暖,嫣赏此风光。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还是挺愉快的。十来个人除高守民外,都是二、三十岁,刘兴邦、小文(公安厅)、老石(他们住甲烈)他们几个是文娱积极分子。竟然将许多流行歌曲印成册子,供大家饭前饭后和休息时间歌唱,《十送红军》我便是那时学会的,而且很喜欢,一个人上路时也要哼哼。
待回忆对比、对敌斗争两项任务在全公社结束时,已到了“五一”前夕。那一段时间,记不清高守民去哪里了。我只好从摆王到甲烈“值班”。五一前夕的晚饭后,大家闹着要去城里玩一天,欢度“五一”。社员开会都是晚上,白天嘛,工作组成员的任务就是走村串寨访贫问苦,为那一阶段的“四清”服务。离开一天倒也无妨,我便答应了。大家又闹着当晚就进城,四十华里呀!大家有说有笑一路好不热闹。似乎不到四个钟头便走完了四十里路(抄近路)。到达县城后,天色已晚。老石和老张是县里干部参加工作组的便回家住,其余住县招待所。老石主动提出第二天“五一”他请客。记忆中大家又赶到县电影院,看了最后一场电影才回去睡觉。第二天老石热情的请了一次客。他一早起来便去市场买回几斤鲜猪肉,做了一盘回锅肉,一盘肉丝,一盘肉沫,还蒸了传统食物腊肉、血豆腐和香肠;又清炖了一只鸡作为压轴,其中腊肉和血豆腐为我之所好,酒喝得不多,腊肉、血豆腐却伴随着米饭吃了不少。待压轴的清蒸鸡上桌时,我已饭饱酒足,几乎不能动箸了。那天下午是怎么回到甲烈公社的,已无记忆,反正是走路回来的。不如昨晚去时那么兴奋,便没有留下半点记忆。
过了两天老高回来,工作组闭门开了两个整天的会,对公社几个干部和十个大队支书,做了认真分析。以便开展下一阶段的“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一个公社副社长便占去了半天,此人已五十出头,成天喜好吃穿打扮,甚至涂脂抹粉,“走到哪里香到哪里”,他引来了工作组内部一番争论。有人说这是作风问题,有人不同意,说作风问题是专用语言,特指男女关系。半年多来没有听到过他这方面的反映。只能说生活不检点,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发展下去,必难避免!反驳者说:对党员处理不能搞预支,发展下去他还可能升官哩!最后老高裁决:无论如何在群众中印象不好,应该免去副社长职务。至于今后怎么用,由区里去定,一场争论暂罢。引起最大争论的是十个支书中的两个,特别是王X荣。此人成天吃喝玩乐,爱酒如命,他有一句名言,“死了也要有一根肥肠子”,更严重的是欺上瞒下,谎报成绩。正逢省花灯团或黔剧团来摆金慰问演出,以示与“工农兵”结合。还指定要去离区里二十里路的甲烈公社演出,步行去当晚回,来回四十里,以表现能吃苦的精神。其中还有一项内容是访问当地“劳动模范”,区里也不知道是谁向他们介绍了王X荣的“模范事迹”。演出过程中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闹剧,演出中途休息时,只见王X荣上了舞台。接下来是一阵掌声,把自鸣得意的王X荣送下台来。工作组内议论纷纷,认为太不像话不能沉默了。便决定由我去找他们团长,说明原因。团长听后大吃一惊,说他们是从区里一个同志的介绍中得知的,说他是修水利的模范,弄得双方哭笑不得,十分尴尬。
工作组对社、队干部进行分析并统一认识后,运动转入下一阶段。召开党员会,用党员标准对照自己,把党员的自我认识与对他人的看法引导至工作组的结论上来,成为弦上之箭,迅速转入组织清理阶段,没用多少时间便大功告成,以开除两个支书,免职一个副社长宣告甲烈的“四清”顺利结束,时间已到五月底。
待到全部公社“四清”完成后,工作团撤至县里呆了两三天,进行全面总结。总结那天县礼堂坐满了人,几个月不见,互相握手谈天,犹如在家接待客人。礼堂内便被嗡嗡之声所淹没。但台上却坐着团长冯玉理,在一片嗡嗡声中,他慢条斯理的念着他的总结稿,直至念完。
结束时说清楚了,这是第一期,回去休息约一个月后,原班人马再回来搞第二批。后来其他人果真又去了,但我没去。原因是机关事情太多,走不了啦。但还得到党校向团长请个假,记得我们是乘机关的吉普车去的,除我以外,还有即将回工作队的刘兴邦和小文。他们在车上等我,我们约好回程时在花溪玩个痛快。
冯玉理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握握手,我说了请假的意思,一说就准,他还反过来问我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后来,大队人马再次下去不到一个月,便撤了回来,贵州党政机关的“大四清”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