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故乡
——金玉龙散文集《陌上花开》读后
□赵雪峰
读了金玉龙的散文集《陌上花开》,才知道:故乡,久违了!
我在“陌上”看见故乡,看见故乡的田垄,梦都开了花。那些山,那些水,那些人,那些事,让我一次次梦回故乡,梦回童年。看到乡亲,听到乡音,感到乡情,记到乡愁……
那山
无论我们走多远,第一步一定是从故乡出发的。那是我们情感的脐带,始终紧紧地拴着我们。所以你在金玉龙的书中看到最多的是“山”,其次才是“水”。“老家多山,本不足为奇,但奇就奇在,这里的山,不是一座一座,而是一丛一丛,如笋如柱,就像被急慌慌赶来,一个惊吓,一个趔趄,突兀兀就立定在那里。”把“静物”写成了“动物”,形容她们“急慌慌”,还打了个“趔趄”,又形容“突兀兀”,把山的慌张,山的动感,山的神态,山摔跤的“趔趄”之态,写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是我见过的写山写得最生动的描述。
看看那些山石。石旮旯的那些石头,有温度。扁担山的石头寨就是石头的世界:石屋、石桌、石凳、石盆、石磨、石灶、石碓、石缸、石槽、石墙,一切,都还是旧时光,时针仿佛在这里凝固了。徜徉其间,每一块石头,都会说话,唤起了每个人一幕一幕的往事。这些石头是有生命的,有记忆的,纪念碑一样的每一块石头,都书写着我们先祖的汗水和鲜血,奋斗和梦想。
那水
抬头见山,低头是河,就是凹河。凹河是条什么样的河,我不知道。但金玉龙说她“低调”“不疾不徐”。对一条河用“低调”来形容,新颖而别致。本身“凹”就是下陷的,在“凸”的反面,在低处,那河水又“不疾不徐”“不卑不亢”“不声不响”,是为“低调”也。“凹河”十分诗意,诗意的凹河像一首乡土诗或爱情诗从山中款款流过,不疾不徐,一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轻轻的我挥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我特别喜欢金玉龙对河岸石壁的描写,“千百年的冲刷,河边上的丛丛石壁,瘦成了千奇百怪的模样。这种丑陋的美,美得残忍,美得孤寂”。几乎全是精美的诗的语言,一个“瘦”字融进多少沧桑,多少迷茫,多少惆怅。
金玉龙笔下的水是甜的,带着使命的。守水,无形中维系了大家唇齿相依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态,一种特定的文化,其核心要义,是团结、互助。
金玉龙笔下的水也是沉重的。家乡的老井,因为搬迁和人员大量进城,而渐渐荒芜。荒芜的水井,浊泥淤塞,青苔横生。煤井机械开采,农田开始失水、变形、下沉,民居也受到影响。又遇山体滑坡,滚滚泥流把房屋夷为平地,整个寨子不得不选择搬迁。一道道令人深思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那人
金玉龙笔下的人物很多,很鲜活。他最擅长把一些凡人小事写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有板有眼、有声有色。在他笔下,几乎没有我不喜欢的人物。
佝着腰,弓着背,时不时鼻子一耸,那两条鼻涕,又顺着来路,梭了回去。他突然飞起一脚,脚下的冰凝,在空中翻了几个颠倒。只见他双手一握,用力一扯,啪地一声,立足不稳,一屁股就坐在地里。手里攥着半截萝卜。这小子,便是毛纠了。
金玉龙这样的白描把毛纠写得非常形象、生动、传神,惟妙惟肖。
三伯伯婚姻不幸,事业不顺,准备去喊冤。虽然身份和补贴得到了落实,但好像大脑受到了刺激,逢人便喊冤,喊着喊着便哭。直到有天晚上三伯穿着那双有特殊意义的大头皮鞋悄无声息离开这个世界。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还有一站,就到了。”整个描述十分揪心,而又寓意深刻。这个篇章完全可以当小说来读,与鲁迅的《祝福》、贾平凹的《树,是会说话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事
说起那些事,太多太多,首先是“那食”。“老家的粮食,一天一天,让我渐渐长大了力气,走出了家乡。家乡的粮食养人,让我脚下走过的一步步,不曾迷失和眩晕。自然,更不敢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忘记回家的路。我无法强求我的孩子,能像我一样对乡村心心念念,但至少,我该让她明白,养大她的,不仅是父母,还有她读过的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故乡,不欠我们什么,而我们,都在欠着故乡,这份债,一生也还不完”。读着他的这些并非简单说教的文字,你会感到颤栗、发怵、一次次感动和疼痛。老家的粮食啊,一粒粒滚过牙缝,承受了若干代人的分量,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源头。无论你走多远也不要忘记来时的路;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不能忘记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老家在哪里。要让孩子们记住老家的粮食和古诗。金玉龙洪钟大吕的文字总让人忍不住一次次冲动,爱不释卷,泪湿纸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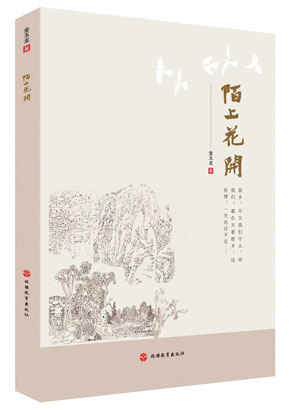
《陌上花开》
金玉龙 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