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变迁的社会学解读
——《陌生的熟人》读后
□范思朦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意图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是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并没有朝老子的意图发展,而在儒家“忠孝”的意识形态之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
费孝通曾经准确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架构,即是按照“差序格局”的秩序来构建的社会形态,每个人都是一个圈子的中心,圈子内外的人亲疏有别,执行着不同的价值和标准。中国传统的村庄正是如此,村民按照一种共同遵守的礼俗和特殊的人际关系逻辑,形成了一个对村民而言具有十分强烈的归属感的自治共同体。在这样的状态下,皇权不下乡,也下不了乡,千百年来,由着这个共同体来维系基层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居然没有出现丝毫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而现在的状况是,乡村的人口逐渐减少,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也面临或者说已经崩塌,农村在凋敝的边缘,“三农”工作成为了我国重中之重的工作。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意图依靠行政、资本、文化、组织、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力量来使农村重新焕发活力。社会各界对于农村的观察和思考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农村土地改革,再到包产到户,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农村一直是关注的焦点。
杨华教授的《陌生的熟人》一书也是观察的结果之一。农村问题的解决,确实是需要多方面的考量。从理论的角度去探究有时候显得不太切合实际,因为农村问题具体到某一个方面,都有强烈的独特性。杨华教授的这本书是基于他多次对乡村的实地考察而得出的一些思考,虽然不能展现农村问题的全貌,但是至少在他观察到的角度,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按照他的描述,农村早已经从互帮互助的“熟人社会”慢慢转变为“半熟人社会”,这也是书名的由来。在一个村庄中,看似再熟悉不过的人之间,也不过是认识而已,之前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以及家族、自治组织对个人事务的介入都荡然无存。村庄从以前的“矛盾不断”回到了“和谐社会”,每个人都不关心他人,也不关心公共道德,只要不妨害“我”的利益,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
《陌生的熟人》这本书的乐趣在于,杨华教授观察的对象实在是有些“刁钻”,他从“泼妇骂街”“群众看新闻联播”以及“婆媳关系”这些事情入手,探寻了一个失去“熟人感”的村庄,而这样的村庄,正是我国广大农村的真实写照。从“泼妇骂街”来讲,以前,村里的妇女相互吵架,一方面是为了赢得这次吵架,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吵架的过程是开放的,村里的其他人会对二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进行一个公正的评价,从而不断强化村里共同遵循的规则。这样的吵架背后事实上是有衡量的标尺的,这也是“熟人社会”的重要标志。但是现在吵架的少了,但是各种道德败坏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情往来也趋向利益交换,这实际上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每个人都与农村息息相关。杨华教授虽然是学者,但是对于农村的观察却并非学者的专属。《陌生的熟人》就是杨华教授抛开学者的“外衣”,以一个“村里人”的视角去解读农村,以随笔的方式来描绘农村,因此书中的文章就有些“非学术化”了,显得十分亲切。
农村问题的改变,必然涉及到文化、道德、产业诸多方面,也并非一日之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面对如此浩大的工程,《陌生的熟人》算是走出了那么小小的一步,其中对于农村的法治建设、道德重建、公共秩序等方面的思考不可谓不是用心良苦。城市早已经是陌生人的社会,一个充斥着“陌生的熟人”的农村,又是我们乡愁的寄居地。何去何从,杨华教授的声音我们听到了,而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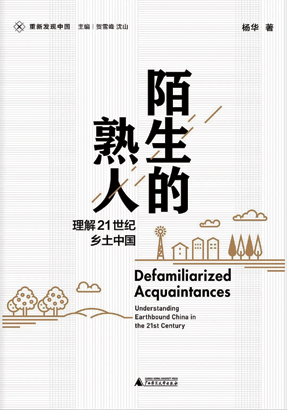
《陌生的熟人》
杨 华 著
贺雪峰 沈 山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