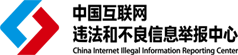月亮沉到了黑夜后
□王彦心
北方的夏夜,于黑暗之中多了一声蝉鸣,虽无那沉稳的静谧,却于万千思绪中多了一丝安心。
我爱北方的夜。
在那儿,几乎每晚,都可以见到一轮明月与四周零落分散的明星。任散落的蝉鸣簇拥双耳,坐在堂屋门口,轻轻摇着硕大的蒲扇,看着奶奶种下的茄子与西红柿安静的生长。慈爱又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妮,夜沉了,该歇了。”我会回过头撒娇道:“奶,你先歇,你歇了,我就歇了。”老人笑着捏了捏碎花布的衣角,迈着小碎步向南屋走去,我跟在老人旁边,只听老人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妮,明个想吃啥嘞?俺给你做。”我搀紧老人的手臂,歪着头说:“奶,我想吃饺子和糊涂(豫东方言,稀饭之意)。”老人打开南屋的门,开了灯坐在床上,嘴里说着:“中,明儿俺给妮做。”侍候老人歇下后,我退出南屋,望着夜空弯大的月亮,心里想着明天应是个晴日。
不出所料,当早晨8点的阳光撒到我的床上时,奶奶的声音一同蹿进了我的耳朵,“妮,起床了,早饭煮罢了。”闻着厨房飘来的香味,我睡眼惺忪的换好了衣服,迷迷糊糊地洗漱了,打开房门,出去和太阳公公打个招呼。我是毫不讨厌这样织满安宁平和的日子的,它虽鲜有波澜,但那温柔的浪花漾在心上告诉我不必担心狂风巨浪。
奶奶走到我的跟前,小心拿出两朵红色的头花来,悄悄地对我说:“这是俺早上赶集买咧,你看你喜欢不?”我从那双满是皱纹的手中看到了两朵红色的假花,小小的惊奇在眸中显露。说实话,在城里,没有这种头花,就算是在农村,平日里也少带。奶奶知道妮儿爱美,喜欢这些新奇的珠花。之前奶奶会在院子里栽各种颜色的凤仙花,常常会摘下几朵留给我别在耳后。但鲜花年华易残,倒不如布面裁织成的花瓣,同鲜绯如生,凝固自己最绚丽的时刻。
我满心欢喜地接过红花别在头上,左右摆摆,问奶奶好不好看。然后傻颠颠地跑去鸡窝找鸡蛋,这是我每早的必走流程之一,可是呀,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母鸡只在冬春下蛋,所以每一天都是空欢喜。也许是年纪小,每天有好吃的就足以将我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也正是这样,那段时光,成了我生命里无可替代的美好。
刚出锅的饺子热腾腾的冒着热气,奶奶调好汁水,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个个送入口中,嗯,那沉淀生活的香味一刹于舌尖绽放,惊艳的姿态抓住那寂寞已久的味蕾。眸深处,涌出满足。这样平逸且生动的日子是永远过不够的,但它总是在某束温暖而舒心的阳光下悄悄溜走,假期结束,我和双胞妹妹踏上回城的路,继续我的初中学业。
城里的风总是很大,把人吹的迷惘四顾,失魂落魄。阴沉的天总是带来不幸的消息,让人变得和它一样灰暗不堪。
农历9月30日,奶奶走了。
父母瞒了我和妹妹很久,只因为那时的我们正在备战月考。
遥远的南方,如同白天,拘着我,没能与月亮见上最后一面,至此,我的月亮渐渐地消失在黑夜后,与那平静的黑色融为一体。
三年又三年,月夜复月夜。
当高考结束后我再次站在小院里时,那些鸡鸭,那些花,那些树,它们灵魂里的生机也随奶奶逝去了,干枯着,给人一种无限的哀伤。
奶奶还是没能看到我考上大学。
再次回去时的我压住心中的苦涩,推开苍老的木门,吱呀的声音像是在责怪我,屋里的陈设都还未发生改变,我走进卧室,昔日挤满温馨的小屋被寂寥和灰色填满。看到窗前的木桌时我忽而想起些什么来,拉开木抽屉试图翻找着那朵红花,所幸,我并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到找了它,可是,花绯赤淡散,枝干变得脆弱,花瓣也只剩下了几片。奶奶的心意也开始随她湮没于无情流岁。我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悲痛,眼泪夺眶而出,喉咙喑哑发不出一丝声音。它是假的啊,为什么会枯萎,为什么,为什么。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实物,现在拥有的一切也终将逝去,连同你的灵魂,回归于这天地。(总说时间斑驳,其实是我们,在时间里斑驳。)
月亮不会消失,它只是暂时蒙上黧夜,它在,还会明亮。
三年了,我站在北方的土地上,望着天上的月亮。奶奶在月亮旁,以后再漆黑的夜,再厚重的云,都不能抹杀月亮的存在。我在心里,守护着,那一轮已然沉入黑夜中的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