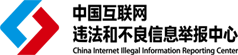树顶暖阳
□甘典扬
近来的冬日,阳光格外懂得人情世故,把积攒了三季的温暖,都细细地铺在这些晴好的日子里。每个周末回老家的路,都像被这暖阳镀了一层金。路旁枯黄的野草在光影中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岁月在抚视万物;路旁的树枝早已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蓝天上勾勒出简练的线条,偶尔有几只鸟雀在枝头跳跃,叽叽喳喳的,为这静谧的冬日平添几分生机。
车子拐进家,轮胎压过路面发出熟悉的声响,像是归家的信号。父亲靠在老旧的靠椅里打盹,那椅子很有年纪了,扶手处被磨得光滑如玉。阳光斜斜地照着他花白的头发,透着暖意,每一根发丝都在诉说着九十多个春秋的故事。他的双手自然地搭在扶手上,手背上的老年斑,像是时光悄悄留下的诗行,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母亲在一旁拌着鸭食,木勺碰着木槽发出“叩叩”的声响——这声音,从我记事起就在这样回响,仿佛这五十多年的光阴都不曾流逝。
两位老人都浸在暖融融的阳光里,像两棵在自家院落里扎根了一辈子的老树,树皮虽已斑驳,枝干虽已苍老,却依然挺立,安静,让人心安。
我轻轻关上车门,还是惊动了父亲。他睁开眼,那双略显浑浊的眸子立刻清亮起来,“回来了?”他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母亲放下木勺,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灶孔里烧有苕,我去拿给你。”类似这样的话在每个周末都会重复,却从不让人觉得厌倦。
闲话了一会儿家常,父亲望着菜园的方向,说道:“柿子都熟透了,再不打该让鸟啄完了。今天你们回来得正好。”二哥便去厢房翻找工具。那间堆满农具的小屋,承载着我们兄弟多少童年的记忆。不一会儿,他举着那柄用了四五十年的“哈谷耙”出来。长长的木柄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耙头上的木齿也都玉溜溜的,握在手里,还能感受到父亲年轻时手掌的温度和我们童年的刻度。我们又找了个塑料漏斗,边缘已经开裂,我用胶布缠了又缠,又紧紧绑在一根长竹竿上。在老家,很多东西都是用惯了舍不得扔的。每一件老物件里,都藏着一段温暖的记忆,记录着这个家的点点滴滴。
菜园里的那棵柿树不算高大,却年年都结出丰硕的果实,像是要把积攒了一整年的甜蜜,都在这个冬日里奉献出来。
高处的柿子最是饱满,像一盏盏小红灯笼挂在湛蓝的天幕上,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向来客致意。有的独个悬着,在阳光下舒展着圆润的身姿;有的三两个挤作一团,窃窃私语着,把枝条压成优美的弧线。阳光透过薄薄的果皮,仿佛能照见里头流动的蜜意——那该是整个夏秋的阳光,都被收藏在这些小小的果实里了。低处的果子则谦逊些,藏在未落尽的几片枯叶后,露出半个羞红的脸,像是待嫁的姑娘,掩不住内心的喜悦。
二哥举起耙子,熟练地勾住一根结满果实的枝丫。他的动作依然如年轻时那般利落,只是鬓角也已染上了霜色。“接好了!”他喊道,声音洪亮,惊起了其他树梢的几只麻雀。我赶紧举起绑着漏斗的竹竿,紧紧盯着他选中的那个柿子。只见他手腕轻轻一扭,柿子便“扑”地落下,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不偏不倚正好落进漏斗里。沉甸甸的手感让人心安,像是接住了一个完整的秋天。
我小心地取出柿子,捧在掌心细细端详。果皮光滑如缎,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泽,果脐处还带着一小片枯萎的花萼,像是特意留下的签名,证明它曾是一朵娇艳的花。
那些最红最大的果实总是最难采摘。它们高高在上,仿佛在考验着采摘者的耐心与智慧。二哥搬来条凳,那凳子腿已经有些松动,站上去时发出“吱呀”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自己的年岁。母亲立即过去扶着凳子,眉头微蹙:“慢着点,凳脚不太稳!”她的声音里满是关切。父亲离得稍远,虽不说话,却也将身子微微前倾,目光紧紧追随着二哥,神情满是关心。他的沉默与母亲的絮叨,恰如这冬日里相生的光影,都是这个家最温暖的底色。
到底有几个调皮的柿子挣脱束缚,在耙齿松开的一瞬间飞快跳开,掉进菜地里。这些已经有了七八分熟的果实经不起摔打,金红的浆汁立刻渗了出来,在黑褐色的泥土上晕开一片甜香。母亲弯腰捡起两个,心疼地拍去沾着的土屑: “可惜了,沾了泥。”
父亲接过去,用粗糙的拇指轻轻掸开泥土:“不脏,还能吃。”说着便熟练地剥开皮,就着裂口吸抿了一口,眼角漾开细密的笑纹:“今年冬天太阳好,在树上晒红的,又香又甜!不像往日打下来还是青的,还要焐在谷子里。”他的笑容里,带着孩童般的满足。
我也挑了个破损的,小心撕开薄皮。果肉颤巍巍的,像凝住的橙色阳光,在指尖微微晃动。我递给母亲,母亲小口吃着,细细品味,不住地说:“真甜,真甜,比往年的都甜。”她的嘴角沾着一点金黄的果浆,像是偷吃了蜂蜜的孩子。
我也迫不及待地剥开一个完好的,轻轻一吸,那股清甜立刻在口中漾开——不是糖的甜,是经了霜露、浸了时光的醇厚滋味,带着阳光的温暖和大地的馈赠,从舌尖缓缓滑进心底。
阳光在枝间跳跃,光影斑驳,时光仿佛慢了下来,只有柿子落入漏斗时“噗”的轻响,和偶尔传来的鸟鸣,还有我们的谈笑声。
树影渐渐拉长,我们开始收拾满筐的柿子,这些温暖的果实,有的圆润如珠,有的略带棱角,每一个都有着独特的形状,却都带着同样的阳光的味道。
父亲望着树梢出神——那里还挂着五六枚最红的果实,在夕照下像是燃烧的火苗,又像是悬挂在树顶的暖阳。
“留着吧!每年不都是这样吗?”母亲说,她的声音在暮色中格外柔和,“给鸟雀过冬。它们也要过日子。”每年打柿子,母亲都要留几个,说这也是行善积德,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
回城时,车里散发着柿子的暖香,浓郁而持久。那是阳光的味道,是时光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照例,启动车子时,父母静静立在暮色里目送我们,总要叮嘱一句:“到了打个电话回家。”这已成为我停车后的下意识思维——报一声平安,让那头的牵挂落地。
我想,那些打下来的或留在枝头的果实,都是父母的爱。他们永远在生命的高处,用最朴素的方式,为我们温柔地红着、甜着。那些留在枝头的柿子,既是给鸟雀的馈赠,也是给明天的希望。而我们这些离巢的鸟儿,无论飞得多远,总会记得归途——因为老家总有一棵树在为你守候,总有一片暖阳在为你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