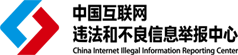冬访毛栗科
□刘燕成
已是深冬,应朋友老冯相邀周末去他的老家毛栗科村游玩。据老冯说,村子就在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满山都是毛栗,金黄的落叶已铺满了山沟,值得一看。
二十余年前,我在贵阳市下辖的开阳县工作时,往返贵阳,就多次经过羊昌古镇,那里后来打造的“花画小镇”,一年四季皆有花香,游人络绎不绝。
毛栗科村还是一个古村落。史料有载,六百余年前,明朝将军傅友德、沐英受朱元璋之令,先后率三十万大军入黔,扎营于贵筑县东下里马堡。毛栗科属马堡十街范围内,明朝军队在这里也建立了大小营盘休养生息。据说,当时驻军及家属常受皮肤病、头顶斑秃等疾病困扰,自然减员严重,正在屯军一筹莫展之时,为逃避战乱自江南而来的女子麻英子在毛栗科深山峡谷之中寻到了一处泉眼,便将此泉秘密分享给屯军及周边村民,不仅解决了饮水之困,日长月久,屯军官兵的皮肤疾病亦不见了。为感念麻英子的恩德,后人便将此泉命名为“麻荫泉”。
麻荫泉至今仍在毛栗科村村委会东侧约600米处的峡谷一侧流淌着。走近看,可见清澈的泉水从井底汩汩冒出,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泛起细微的波纹,游鱼快活地随着泉水的涨落从山涧深处进进出出。低头细探,便又发现有丝丝缕缕的白雾从水面蒸腾而起,像是锅炉上的水汽,往天上飘。
泉边的石碑上刻着麻英子的故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老秀才写的,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却字字都透着敬重。石碑旁的野菊已枯,只剩干瘦的花茎还在风里晃,倒让这段传说多了几分沧桑——仿佛麻英子还站在泉边,手里攥着竹管,看着泉水顺着竹槽流进寨子里的水缸。
村里《周氏家谱》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年,携妻带子,负粮入黔,过都柳江,越苗岭,见此山多毛栗,泉甘土肥,遂伐木筑屋,垦荒为田。村里人说,康熙初年从江西迁徙而来的周氏先祖,把毛栗科村发展壮大。之后,迁居于毛栗科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马堡十街原本就有李、冯、袁、白、文、赵、吴、何、周、包等十大姓氏,就让高寨、榜上、大洞、大园、水沟、龙滩、小奋田、何家洼、石灰窑等十余个自然寨,都慢慢有了炊烟。到民国初年,“科”字融进了村名——“科”是“窠”的转音,暗喻古老的毛栗科村像鸟儿在毛栗树间筑的窠,裹着山里的暖。
村子里的确有满坡的毛栗树,北风吹来,一片片残剩的黄叶纷纷飘落,把山谷染得更黄了。层层叠叠的落叶下面,除了暗藏着麻荫泉,还深埋着一个神秘山洞,人们称其为“神仙洞”,从麻荫泉往山谷里前行百来步即到。走近细看,只见洞口结着薄冰,像蒙了层纱,只容一人侧身进去。岩壁上的青苔覆着白霜,润润的水汽裹着草木的冷香扑过来,往洞里走几步,光线就暗了,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以及深洞里水滴的“嗒嗒”声。水滴落在石上,凝结成一串串细细的冰凌,像挂在洞里的水晶。
观过村景,我去拜访了毛栗科村的袁大贵老人。老冯曾说过袁大贵老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就像毛栗科村的毛栗树,人人都知道。1930年出生的袁大贵,1950年听说部队招兵,揣着娘蒸的红薯干,瞒着家里人报了名。后来跟着部队去了朝鲜,上甘岭战役里,他的左手腕被炮弹皮划了道大口子,至今冬天还会隐隐作痛。1955年他回了乡,先在乌当区收购站管过粮食,可心里总惦记着家里的农田,没多久就回了村,跟着生产队种水稻、薅玉米。我们在他家堂屋见到他时,老人正坐在藤椅上,盖着厚棉被,身上穿的棉袄洗得发白,手里攥着一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章面已被摩挲得发亮。老人有些耳背,声音也有些沙哑。说起朝鲜的冬天,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那时候比现在冷十倍,雪没到膝盖,我们趴在雪地里,一动不敢动,饿了就啃冻硬的土豆,渴了就抓把雪往嘴里塞。上甘岭的石头都被炮弹炸成了粉,我受伤的时候,鲜血把脚下的白雪都染红了。当时以为活不成了,可一想到家里的毛栗树,想到娘还在村口等我,就咬牙挺了过来。”回村后,他把部队严格细致的规矩用到了种田上,冬天修田埂、挖水渠,夏天顶着太阳侍弄庄稼,他的田总是长得最好的。现在老人走不动田埂了,每天还会坐在门口,看着远处翻耕的土地,见有小孩路过,就拉着说:“以前冬天哪有现在这么暖和?现在有水泥路,有路灯,有学上,还可吃饱饭,这都是我们当年打仗时盼着的日子啊。”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现在的毛栗科跟以前不一样了——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路灯照得夜里亮堂堂的,污水处理站建起来了,整洁漂亮的一栋栋民宿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省内外的游客来了一茬又一茬。但不管村庄怎么变化,村口的毛栗树还守在那儿,麻荫泉的水还在周期性地涨落,神仙洞的传说也还在村里流传着。走到村口,又看见一棵棵百年毛栗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深褐色的树皮上覆着白霜,像裹了层糖霜。枝丫间藏着圆锥形的冬芽,像攒着劲儿,等着开春迸发。北风一吹,枯枝“呜呜”地响,像是老辈人在说着什么。我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的粗糙蹭着掌心,冰层下却透着一点温乎——那是毛栗科人代代传下来的韧劲儿,是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暖。
夕阳往冯家大坡山后沉的时候,冬阳把毛栗科村的天空染成了淡粉色,像撒了把桃花瓣。毛栗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盖住了田埂上的冰碴子。贵开快速铁路的列车从村子中央掠过,轰鸣声越来越远,村里的炊烟慢慢升起来,混着柴火的焦香,飘在屋顶上。我们走在村里的小路上,路过何家洼的溢寿井时,看见几户人家的屋顶上,太阳能热水器的管子结着薄冰,像挂了串冰糖;路过龙滩时,水库表面结着一层薄冰,几只水鸟落在上面,啄着冰面找鱼,爪子踩在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那些散落在前毛栗科和后毛栗科的漂亮民宿,落地窗上挂着火红的夕阳,晚归的山鸟从窗前飞过,停顿了半晌,仿佛是舍不得离去。
月亮悄悄升了起来,挂在毛栗树的枝桠上,清辉洒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洒在冬田的稻茬上,洒在育苗棚的塑料膜上,洒在每一户人家的屋顶上,也洒在袁大贵老人手里的纪念章上和毛栗科人的心坎上。我知道,从明朝的驻军屯堡,到如今的小康村,毛栗科经历了六百余年漫长的春夏秋冬,可藏在这一季深冬里的故事,还在继续。历史和往事并未灰飞烟灭,我相信那些深埋在树影里和泉声中的光阴,会像麻荫泉的水一样,慢慢流,慢慢淌,在毛栗科大地上,续写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