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战地记者的深情独白
——读《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
□周广玲
《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一书的内容创作于1952年抗美援朝时期,以作者随巴金率领的“赴朝创作组”在朝鲜前线八个月的经历为背景,融合战地日记与家书两种文体,记录了志愿军前线生活、作家群体创作活动及朝鲜军民的真实图景。
全书收录1952年6月至10月的战地日记及同年2月至11月的32封家书,通过亲历者视角展现战争叙事与家庭情感,同时呈现前后方互动情景。书的编撰者为李蕤的女儿宋致新,部分内容为近年新发现并首次公开,为研究抗美援朝时期文艺工作者活动提供了史料。
1952年3月,41岁的作家李蕤与母亲和四个年幼子女吻别,毅然背上行囊,奔赴朝鲜战场。作为巴金率领的十七人“赴朝创作组”成员,他本可在后方以笔为援,却选择与志愿军一同投身炮火纷飞的前线。
在九个月的战地生涯里,32封家书与108篇日记从坑道中源源不断地传出,宛如雪地上的鸿爪。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珍贵文字凝结成了《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翻开那泛黄的纸页,硝烟与温情瞬间扑面而来。“孩子们!爸爸已经穿上志愿军的衣裳,戴上志愿军的帽子了。现在要是你们看见我,肯定都认不出来啦。你们不是都很喜欢志愿军吗?现在爸爸也是其中一员了。”初到朝鲜的李蕤,在给儿女的信中难掩内心的自豪。这位曾因反对国民党统治两次入狱的作家,将赴朝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当穿上志愿军军装的那一刻,他的笔尖仿佛与枪杆紧密相连。
战火中的文字之所以无比珍贵,正是因为它们本就不是为了发表而存在。家信是对儿女的深情私语,日记是自己的内心独白。正因如此,它们毫无修饰地保留了历史的原汁原味。透过这些带着体温的记述,“最可爱的人”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灵动的生命。李蕤的笔触格外关注普通士兵。在开城前线,他记录下许多感人的身影:电话员在电线被炸断的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接通电流,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导线,确保通信畅通;担架员背着伤员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还不忘为前线捎去弹药;炊事员每日要跋涉四十里山路为战士们送饭,肩头磨出了厚厚的血痂。
面对这些事迹,李蕤在信中感慨:“这不必找什么英雄功臣,一个最平常的人身上也能看见。”而当读者为这些英勇壮举惊叹时,战士们却总是平淡地说:“我们没为人民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伟大与平凡在这里相互交融,铸就了真正的英雄丰碑。战地生活并非只有残酷的炮火,在换防休整的山谷里,李蕤捕捉到这样一幕温馨场景:“早上一睁眼,四周便传来‘玻坡摸佛’的拼音声。”年轻的通讯员满脸骄傲地告诉他,战士们正在突击学习文化,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认识两千多字。这些在生死线上拼搏的年轻人,心中依然满怀对凯旋后建设祖国的美好憧憬。当祖国慰问团前来演出时,坑道里响起的沸腾欢呼与流淌的激动泪水,又让人看到他们其实也只是一群想家的孩子。
书中最为动人的篇章,当属李蕤与巴金、魏巍一同奔赴前线的经历。三位作家冒雨穿越 159 高地的生死线,在没膝的泥泞中艰难前行。巴金不慎跌倒后,爬起来只是平静地说:“不过我还有力量支持下去,站起来,就继续往前走。”敌机在头顶盘旋时,他们趴在炮弹箱上坚持写作,一夜之间数次吹灭烛火;采访英雄时,又常常自责笔力不够,难以描绘出战士们高尚品质的万分之一。这些文学大家在前线甘愿做求知的小学生,他们的背脊在雨中升腾着热气,恰似民族精神在战火中不断淬炼升华。
在日记本褐色的封皮上,李蕤以遒劲有力的笔锋写下“鸿爪雪泥”四字。七十载岁月匆匆而过,这些雪泥鸿爪已然成为无价的珍宝。当读者跟随当年年仅三岁的“芽新”——如今已是七旬老人的宋致新的视角,重读父亲穿越战火的家书时,仿佛能够触摸到历史深处留存的余温。黄继光牺牲前给母亲写信说:“现在虽有少些困难,是能够渡过去的,幸福日子还在后头呢!”竟仿佛是跨越时空的预言——他们用生命点燃的星星之火,最终汇聚成了今日的万家灯火。
这部由弹孔与墨迹共同铭刻的日记,成为我们理解“最可爱的人”的精神密码。书中没有宏大叙事的华丽光环,只有坑道里摇曳烛光下,一位父亲对儿女的深切思念,一位作家对战士的由衷敬仰,以及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当合上书本,那句“来,让爸爸亲亲你们吧”的轻声呼唤,依旧在岁月的长廊中久久回荡。原来英雄亦是平凡人,而平凡人亦能成为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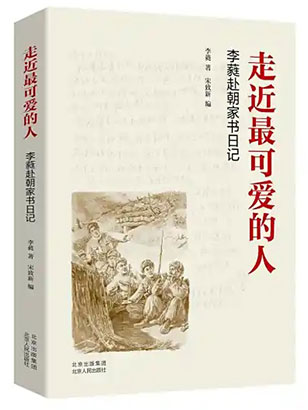
《走近最可爱的人:
李蕤赴朝家书日记》
李 蕤 著 宋致新 编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