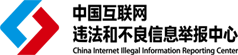牛场的色彩
□黄树生
一
牛场,我是第二次到这里来。第一次时,扒着地图看,贵州可能有几十个地方叫这个名字,好不容易才在六枝的山山水水中找到它。这一次,几条河流把它隔成了“黔中宝岛”,青青绿绿的,真是一幅以山作纸、以水为笔、各种色块浸染的多彩画作,成了我最直观的感受。
开场便是天然写意。清晨刚下过雨,天空中还有断断续续的银线,把眼睛洗得清清亮亮。高速公路在山岭间穿梭,车一猛子扎进雾里,又从不知何处的隧道口出来。山高云深的地方,青山模糊、白雾缭绕,那些不规则的青绿、灰白互相穿插遮掩,叠加融合,大片灰白里漏出一些黄色和黛青。那是散居的人家,像传说里的避世桃园。走向不同、高低不同的那些山,此时蒸馒头一般冒着白气,白气漫无目的逸散开来,向人迹罕至的谷壑流淌,或涂抹着天际。顾盼间,整个画面“活”了起来。
车终于在一处半山腰停下来。下了车,大家迫不及待为眼前的风物拍照。我惊叹于所处的位置:山峰最高处的陡峭,古树盘虬,岩石袒露,似断墨存意,又似画面“留白”。山脚是郁郁葱葱的竹林,几间小巧别致的瓦房,有烟火的痕迹,有田园的诗意,有自然的野趣。
眺望谷底,河面宽阔舒展。大雨甫定,水面裹挟着泥沙,泛出淡淡的赭褐色,更像一部惊心动魄故事的序言。
二
河是“三岔河”,当地称“懒龙河”。我们在河滩平缓的这边,对岸则是一仞几十丈高的悬崖峭壁。
那峭壁上,早前也曾经住人,还发生过战斗。牛场乡宣传委员告诉我们:解放初期,著名的“绝壁天险窗子洞”战斗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现在是解放军剿匪战斗的一处遗址。山壁中间有一道明显的凹痕,那是“跑马道”——峭壁上一条人工挖出来的可供人行马跑的道路;那一个个“黑点”,好似山体的大小“窗户”,其实是悬崖上天然溶洞的出口。
宣传委员绘声绘色地讲述着71年前那场战斗。解放初期,国民党一残部带领匪众,据守在对岸悬崖峭壁上的溶洞里。解放军派出3个营围攻,在付出7名战士生命的代价后成功擒拿匪首。
想象着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绝壁上的硝烟还未散尽,那些嵌在岩缝里的呐喊——战士冲锋时嘶哑的怒吼、溶洞里震荡的回响、金属与岩石的碰撞——如今都沉进了斑驳的色块中。
此刻,山风掠过弹痕,把当年的喊杀声纺成雨丝;曾经震耳欲聋的爆破,正被鸟鸣一声声啄成清亮的露珠。仰望悬崖上方的“龙桥烈士陵园”,战士们的热血早已汇入溪流,忠魂亦化作春泥,滋养着这方热土。
抗战时期的“安家碉楼”依旧耸立在不远处的上官寨山巅,威风凛凛,不肯卸下守卫村庄的重担。尖岩村的茂密树林里,“织普郎边区游击队”指挥部旧址依旧。那些木夹石的建筑,历经一个世纪,依然能为我们遮风挡雨,偶有几栋水泥平房突兀地插在传统屋舍间,摇曳的灯光亦证明着山里人家的坚守。
孩子们陆续走出了大山,老人们则坚守着斑驳的老屋。在村子前面的说书亭里,孩子们痴迷地听着老人们永远讲不完的战斗故事;那些褪了色的门楣上,端正装裱着伟人的头像;这里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自然,这里的百姓也生活得那样自由恣意,这些鲜活的坚守,以最质朴的方式延续着村庄的传承。
三
沿路都有人家。他们把家安在花园里,前有花,后有树,院子宽宽的,主人家见客带笑。
那些才有木篱高的孩子们含羞带怯,好奇地打量外来的人和车。脸蛋红扑,眼睛水灵,哪里唤一声,就跑开了。他们是牛场的未来。
行走中闻到枇杷的味道。这里道路两旁、房前屋后都是散栽的枇杷树。五、六月天,浓密宽厚的叶子间挤满了铜铃般的果。风一吹,黄的颜色时隐时现,那些色块嫩嫩黄黄的,青黄也有,未熟的果没有人摘,更没有人破坏,哪怕站在路上探手可拿,它们就这样放肆地将色块往湛蓝的天空里挤,好让更多的人闻到它的香。
这是牛场的特产吗?我询问,宣传委员笑而不答。直到饭点才知道牛场的特产是另一种颜色更显眼,情绪更热络的东西。
一大盘油炸辣椒被端上桌子。紫红的辣椒簇拥着,配上一碟蘸酱,让客人食指大动。胖胖的辣椒圆头细尾,用手抓一根,蘸上酱,吃一口,外酥里嫩,唇齿留香,微微的辛辣中似有甘甜。简单干练的吃法,一如牛场人爽利的性格。店家介绍,油炸的要点在于火候,过火焦了就有煳味,火候不够,内里又生。看似简单,藏着匠心。宣传委员说做法易学,原料难得。因地理气候因素,辣椒体大肉厚,色泽鲜艳,营养丰富,有别于其他——这才是牛场的特色。
火红的辣椒铺就了牛场人生活的底色,诉说着乡村振兴的故事。

牛场风光

龙桥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