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需要发现更需要创造
——记民盟盟员、著名画家潘闻丞
编者按:
科学征服世界,艺术美化世界;理性素质让人有征服世界的力量,感性素质则让生活富有诗意;没有科学,人类是软弱无力的,没有艺术,人类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已经大幅度提升,但是,从“获得感”到“幸福感”之间还有距离,这个距离并非物质堆砌所能满足,而是要依靠精神生活的提高,以及感性素质的加强。
本文记录了贵州画院院长、贵州美术馆馆长潘闻丞的艺术生活二三事,从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领会如何在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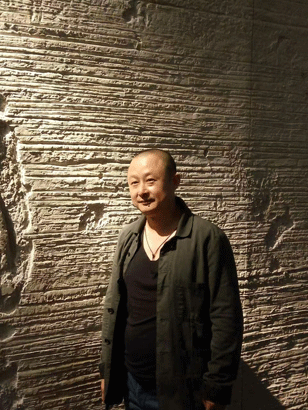
潘闻丞: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学会理事,贵州画院院长,贵州美术馆馆长,贵州油画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美术师,贵州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本报记者 万里燕
艺术是高岭之花。
即使在资讯发达、文化繁荣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种种方式领略各种展览,很多人依然认为艺术和生活还是有一定距离,艺术家也大抵属于不好接近的一类人。但潘闻丞仿佛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力,“朋友遍天下”这句话在他身上一点也不为过。而这种亲和力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
我与潘闻丞相识已6年有余,其间看过不少他的画作,每次都有新的惊喜。
潘闻丞的画,题材涉猎广泛。
初识时,他在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当秘书长。那时的省美协办公地点在花果园国际商务中心顶层,倚窗就能看到人称“白宫”的地标建筑。这栋建筑曾经被拍过不少照片,也入过一些画家的选材,但以居高俯瞰的视觉角度、以油画的形式来表现这栋建筑的,我所知的仅潘闻丞一人。想象一下潘闻丞临窗而画的样子,颇有“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触动。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不时会看到潘闻丞的作品,惊叹除了建筑之外,静物、风景、人物……一切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都可入他的画,并且变得艺术感十足。
比如风景。潘闻丞热爱写生,他曾把一辆吉姆力越野车改造成为专门的写生用车——底盘加高,轮胎加宽加粗。改装后所有的绘画工具都在车上,随时停下来,随时可以画。而且还能画1.6米的大幅作品,非常的方便。在当初工作不那么忙的日子里,潘闻丞时常不是在写生的路上,就是在去写生的路上。然后诞生了众多的风景写生——山、水、花、草、木、天空、民居建筑……。看着这些画,好似通过潘闻丞的眼睛看风景,淡雅又深刻。
潘闻丞的画,表现手法多变。
今年是虎年,春节刚过,一幅潘闻丞的木刻版画《虎年大吉》刷爆朋友圈。“版画可以多次印刷,所以这次尝试用版画手法创作了这幅作品,可以多印一些送给朋友应景表示新年祝福。”潘闻丞认为,艺术都是相通的,不该拘泥于表现形式。不只版画,潘闻丞也有相当一段时间尝试国画,他的国画作品《鼓楼·城楼》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他尝试在在中国传统水墨的干湿浓淡的基础上,巧妙结合油画立体塑造,无论从
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在意境的表达上,都具有非常独特的“潘闻丞式”高级感。
由于越来越忙碌的工作和疫情影响,很久没听闻潘闻丞再外出写生。偶有一天,阳光明媚,与潘闻丞通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楼下写生。随后微信发来一张照片,他的身边两辆推车,一辆上面全是油画工具,另一辆上面是两只猫笼,装着他的两只猫。他说,今天天气正好,远处去不了,画一画家附近的风景也是好的,顺便让两只猫晒下太阳。原来画家写生不一定要去远方,家门口也有独一无二的风景。
今年年初,潘闻丞担任贵州美术馆馆长,行政事务变得更加繁忙,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有很多时间和精力画画了,但他依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在绘画的题材和技巧上,变得更加收放自如。
前些天,一位教授在美术馆做了一场讲座,过了两天,潘闻丞就在画布上重现了这个场景。潘闻丞也坦言,他并不擅长画具体的人,因此画面里的讲座,即使有那么多听众在场,但他皆以笔触来作面部表达。虽然看不到面部表情,但短而密集的笔触,不仅把观众的轮廓勾勒出来,更将讲座热烈而专注的氛围溢于画面之外。这幅画的处理手法,让我想起他在第三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中获优秀奖(最高奖)的作品《哀悼日》。在这幅宽3米五、高2米的作品上,上百人正在哀悼汶川地震遇难者。画家并未刻画人群的具体面部,自然也没有表情描写,而是通过沉重的笔触和灰暗的色调,让那种灾后凝重且悲情的场景跃然于画布之上。相比于数年前《哀悼日》的着力刻画,这幅《桑教授的讲座》,可以看到如今的潘闻丞在氛围表达上更加精进,能够在自由的笔触中和对色彩的精准把控中,进行更为轻松且到位的表达。和别的工作不同,要成为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艺术家,尤其需要天赋和积累,而艺术家的艺术生涯中不同阶段的作品,都是其人生的总结和表达。
潘闻丞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潘闻丞和艺术的结缘来自于一次搬家——新家位于当地文化馆附近,邻居大多是文艺圈里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这让年幼的潘闻丞接受到了艺术的熏陶。
那时没有艺术班,父母工作忙碌,更没有“逼迫”潘闻丞学艺术,这反而打开了潘闻丞自由探寻艺术的大门。很多时候,他自娱自乐,或用石头,或用画笔,在地上或墙上涂鸦,在这个过程中,他和艺术慢慢靠近。正是如此,潘闻丞的艺术之路一向自由且随心。
不久前,“湖北·贵州 现在时”画展在贵州美术馆进行展览,我与友人前去观展,在一百多幅参展作品中,友人指着潘闻丞的油画作品《搁置物》表示最喜欢这幅。仔细一看,这幅长3米六、高40厘米的画中这些瓶瓶罐罐,不就是他工作室桌子上放的那些嘛!原来,潘闻丞的艺术已经大道至简,整个世界都是可以尽情挥洒的画布。
几朵插在瓶子里的花,成了梵高的名画《向日葵》;几面普通的钟,成为达利传世之作《记忆的永恒》……最好的艺术家,永远是最擅长观察生活、描写生活的艺术家。诚如贵州油画学会会长、贵大艺术学院教授赵竹的评价:“潘闻丞的画离时尚很远,离自己的心性很近。绘画,一种成瘾的行为,成为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罗丹说:“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美,我们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回到本文第一句话,艺术真的是高岭之花吗?我想,潘闻丞在他的艺术理念和实践中,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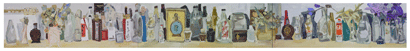
油画《搁置物》 潘闻丞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