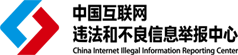那年的声音
□胡长斌
那个时候,每到下午放学,学生走了,老师走了,宽阔的大操场显得空荡而落寞。
操场西面北面边缘小山岗下,散落着十数户农家。农家后面顺坡上行修建有三排教职工宿舍和学生寝室,三二个老师还住在那里,其余全都空着。农户人家大多姓骆,也有姓蔡的。向晚时分,偌大的操场上,偶有一只二只吊儿郎当的黔北黑山羊咩咩着,还竖直羊尾巴,拉上一团一团黄豆大小的粪便,在主人的呼唤下,懒洋洋地朝操坝边上的羊圈走着;谁家一匹大红冠子的公鸡,飞扑一只正在草丛啄虫的母鸡,公鸡咯咯叫着,半张着倾斜的翅膀,围绕母鸡绅士般舞蹈……
不经意间,夜晚降临,地处操坝东面临堡坎的地方,孤零零站着一幢房屋,历来作办公室之用。而现在,则为我一家所有。堡坎下面是两排教室,长长的,在夜幕下渐糊渐黑。
我的忧郁,便随着夜晚的来临而盘桓心头。
关于忧郁,不是来自于工作,亦非来源于生活的清贫,而是听到了一种声响。说声响,可能不太准确,因为不能确指响动于何事与何物。那末,应该说是一种奇怪的声音吧,即物体的振动波通过听觉而产生了印象。
要准确描述那种声音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似乎十分宏大的声响,具有铺排之势,心神为之倾倒;又似乎极为细末,细微到像从久远的荒原传过来的劲风之余韵,不见其力,但能感觉存在。
这是三十年前的感觉,历三十年的磨砺,以当下的心态,窃以为,要准确把握那种声音,就要对那幢办公室作必要的说明。
那栋房,产生于大炼钢铁年代。一开始,就是作为办公室修建的,办公室前面,是一片高低不平的田块或不高不大的山堡(后辟为大操场),周围散落着耕种的农户。办公室下面是一片下行的缓坡,或沟壑纵横,或杂木刺蓬丛生。以后,将缓坡建成几座铁炉,举正安北部(今道真全境)之力,大炼钢铁,在铁炉周围,堆满了成千上万的毛铁,层层叠叠,形成若干小山。当年,几位苏联专家及指挥部人员就居住在办公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道真恢复为县,钢铁时期留下的房屋及少量土地,成了关押犯人的地方,办公室又成了管教中心。六十年代中期,管教中心不在了,办成一间完全中学,即“道真中学上坝分校”。办公室成为校长办公室、财会后勤服务室、体育器材室。七十年代末,道真中学上坝分校改名上坝中学,属教育局直管,仍为完全中学。八十年代初,将上坝中学改建为道真县职业高级中学,几年后,又将职中搬到县城德村寺的新建校区,便遗下一大片遗产,包括师生历时十数年修建平整的大操场,经过艰苦奋斗修成的数十间教室。一九八七年初,我调入上坝乡属初级中学,上了半学期的课,因校址普明寺改建,全体教职员工及学生利用职中(钢铁厂)弃置的教室与操坝,搬到钢铁厂上课。这时的校名仍叫“上坝中学”,但与原先的“上坝中学”不是一间学校。此时学校的老师在普明寺大多有住房,亦有县城的,放学之后,他们骑上单车,走了。开初,办公室还住过老师,后来他们也骑单车回家了。我就搬进了办公室。
关于办公室,坐东向西,两层砖房,苏式结构,两面山墙青砖封顶,成两面流水。檐面用木条封闭,四围无风进入楼上。楼上楼下,开有玻璃大窗,窗外有铁条防盗。楼房有四间,其中右面三间为钢铁年代所建,左边增设一间,属“上坝分校”所置,所建的一间与三间一个模式,让整幢房屋外貌一致。原建的三间木楼板贯通,在左面一间修了木质楼梯上楼,全封闭楼梯。外面的小门上了锁,就没法上楼了。以后新建的一间作为后勤专用,在原建的山墙上开了一个门,以便充分利用全封闭的木楼梯背面的楼梯间堆放一些锄头之类的工具。
某个夜晚,我去楼梯间清点喂养的鸡,无意中听到了一种声音。我觉得可能是楼上有甚么东西让风吹动,在楼梯上作响。凝神静听,外面无风。我又想,可能有一只顽皮的老鼠,闲来无事,在楼梯上撒欢吧。可是,那声音,绝不是外界有甚么物体接触楼梯而产生的声响。
那声音,近似于高跟鞋轻叩木板的响动,咯咯咯!嗑嗑嗑!不轻不重,不徐不缓,不紧不慢,不漂不移,始终如一在楼梯上响动。楼上堆满职中尚未搬走的课桌,外面是一把铁将军把门,不可能有任何高手入室,无钱无财,他去干嘛?然则,这种类似于高跟鞋轻挪移步于楼梯上的声响,我行我素,响彻于漫漫长夜。
倘若月黑风高,屏息而听,那声响恍如一匹孤狼在洪荒岁月中的嗥嚎,长而不息,远而留声;电闪雷鸣之际,那声响似乎也已远在十万八千公里以外,绵远不绝,细而不断……有一回,我心烦了,用锄把敲打楼梯板,而那声音依然不绝如缕,缭绕其间。于是,我明白了,没有任何一种外力,可以迫使这种声响销声匿迹。
那时,孩子们学习和睡觉在右边第一间,顺数过来第二间是堆放柴火,全家吃饭的地方,相当于厨房,比省长的厨房还大,第三间前面临操场是一间卧室,正是我和家属下榻的地方。卧室后面空间空置,堆放一些家具,有一道门进入楼梯间,关上几只鸡。因为照看鸡,这才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孩子们还年幼,老婆又胆小,楼梯间的声音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听见。所以,傍晚之后,就督促孩子们完成作业,洗脸洗脚睡觉;老婆有事去家具间看看,我自告奋勇前往,不让她接近楼梯间,当年,在那幢房屋生活了几个月,始终没让孩子和老婆知道我听到的声响。公元一九八八年初,我调离上坝中学,供职县志办,和吴守业先生等人一起编纂县志。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碰上当年在上坝中学管财务后勤的冉老师,恰又碰上来家作客的韩老师,这二位都是当年我在上坝初级中学教书时的同事,闲谈中,偶尔提及当年我在上坝钢铁厂那幢孤零零的办公室楼梯间听到的声响。冉老师说,你别说了,太惊吓人啦!当时我也听到过,就再不愿住那里,宁愿把账本之类的装在一个大挎包中,骑单车回家。韩老师也说,哎呀!我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老婆大叫:不说了!不说了!真是吓死人哪。
冉老师心有余悸说,你就不怕吗?
韩老师是女性,战战兢兢说,没想到……那房子……好可怕!
说到“怕”,说真的,我一直没有怕的感觉,只是忧郁而也。忧郁甚么?至今也难理个明白。倒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那种声音吓坏家人!
关于那声音,在心中一直留下一个谜,想破解,却无从着手。近年,看了中央纪录频道的一个栏目,或许可以为这种奇怪的声响作一个解释吧。
专家说,有一种虫子,特别爱钻阴暗环境下潮湿的木材,这种虫子钻进木材之后,在里面打成洞,变为它的家。饿了,就啃木材吃。吃完了,就将木屑吐出来,成细屑状散落在木材周围。这些细粉类的木屑吸收水分或潮湿之气,又加快了木材的腐烂。
虫子在吃木材时,肯定会发出声音,这就是我听到的那种奇怪的声响。为何总是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才能听到?其实,虫子一直在吃木头,只是外面有声息,马上就把虫子的声响掩盖了,听不到了;到了晚上,这种声响因为没有其它声音的干扰,兼之环境封闭,空间狭小,便容易让人捕捉到虫噬木头的声音。
至于这种虫噬声或强或弱,客观上与虫子的着力有关,主观上还与人的心情相联。倘若产生错觉,甚至还会感觉到嗑嗑声在楼梯上下有规律地移动,正像一个徘徊不定的人上楼梯下楼梯,再上再下,反复如斯……有好几次,我就有此感觉。我不信鬼,一点不惧。只是这种上上下下的嗑嗑声,徒添了许多的怅惘。产生这种错觉的缘由,除心理因素外,恐怕还与虫子接触木板的方位、方式和方法有关吧。当然,我无法亲眼目睹虫子噬木的情景,以上文字,大致算是我的臆断吧。